荆培运系统准确地理解儒家思想的哲学原理与原理
荆培运系统准确地理解儒家思想的哲学原理与原理
■荆培运
系统准确地理解儒家思想,首先必须厘清它的哲学原理。只有把握了那条“红线”,才能将散落的“珍珠”串成美丽的“项链”。为此,让我们先行考察儒家一贯强调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等范畴,是否就是它的哲学原理。
仁。孔子对“仁”的解释主要有:“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人也”;他还特别赞赏颜回“仁者自爱”的提法。可见在孔子心目中,“仁”的基本含义就是自爱与爱人,是对“人”这种生命体的基本态度。孟子关于“仁”说法与孔子一致。
义。孔子指出:“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要求人们对待事物,不要有先验的“行”或“不行”的成见,而要站在正确的一边。“义者,宜也。”义,就是适宜、正确(的道义或原则)。孟子进一步指出:“义者,人之正路也”,并将“义之与比”提升到“舍生取义”的高度。
礼。“礼者,理也”;“夫礼,所以制中也。”在儒家心目中,礼就是协调关系寻求平衡(的手段)。广义的礼是协调关系寻求平衡,狭义的礼就是“仪”。
智。孟子说“是非之心荆培运系统准确地理解儒家思想的哲学原理与原理,智也。”明代王阳明“知善知恶是良知”的“良知”,跟孟子所说的“智”,有着明显的联系。简言之,智,就是判断正误的能力。
信。孔子说过“民无信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这样的话;他的学生曾子和子夏等人,也多次提及“信”。董仲舒将“信”与仁义礼智并列,构成所谓“五常”。信,就是既不自欺,也不欺人。
忠。孔子主张“臣事君以忠”,但不主张愚忠。秉持“义之与比”“当仁不让”理念的孔子,是不可能无条件去“忠”的——“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孝经·谏诤篇》:“子曰:‘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孟子则认为,杀掉商纣那样的暴君是符合道义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孝。孝敬父母,与恭顺兄长合称“孝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以孝悌为出发点,将对父母兄长的感情扩展到一般人身上,由爱亲到爱人,就是“仁”,亦即孔子所说的“立爱自亲始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和哲学思想,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孟子总结得很对。
显然,无论仁义礼智信,还是忠孝,都只是某一方面的具体准则而非总的原则,本身不能上升到哲学原理的高度。从孔子的论述和儒家行为的共性来看,中庸,才是儒家思想的哲学原理。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作为一项原则,是至高无上的。中庸,亦即平衡与适度的原则,与《尚书》“允执厥中”、《易经》“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论语》“过犹不及”、《孟子》“不为已甚”乃至《老子》“去甚去奢去泰”,都是一个意思,是朴素的、中国式的辩证法——真理再往前一步,就可能变成谬误。遗憾的是,儒家没有合适的语言工具来表述它的辩证法,佶屈聱牙的古代汉语不具备这项功能。因此他们的学说既没有严密的逻辑形式,也没有动人的神灵故事,更没有“末日审判”和“地狱”的恐吓,而把貌似“老生常谈”的智慧结晶,以“箴言”的形式直接呈现给人们,这使中庸成为最感性的最不思辨的辩证法。
孔子说:“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为什么中庸如此难以达成呢?因为它不是一个静态的东西,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阶级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相互矛盾,冲突是绝对的,妥协是相对的;今天找到了各方利益的平衡点,明天,随着环境的改变,旧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只有用中庸亦即平衡与适度的原则不断协调各方的利益诉求,社会才能“生存”下去。也就是说,中庸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但它是社会的生命线。基于这一原则,儒家在经济和政治等领域一直追求适度的平衡,这一点,长期以来未被充分认知。例如:
基于中庸亦即平衡与适度的原则,在经济领域,儒家强调“不患寡而患不均”。“寡”,生产资料和社会总产品的不足,是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退一步讲,就算生产资料和社会总产品有所增加,要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也必须理顺分配机制,以国家的力量来调控分配,“周急不继富”,以达到经济利益的相对均衡。可见,儒家的“均”,一开始就是从整个“社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哪一个阶级的利益出发提出的主张。在儒家眼里,个人与社会相比,永远是次要的。对少数既得利益者来说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和哲学思想,“均”意味着剥离而不是增加部分利益。当然,剥离部分利益的“利益”是维持其统治从而收取长远利益。对大多数民众来说,“均”不可能让他们“撑着”,但也许能避免饿死。如果不“均”,剥夺者将被剥夺,社会将在激烈的冲突中走向周期性毁灭。儒家要防止的,正是这种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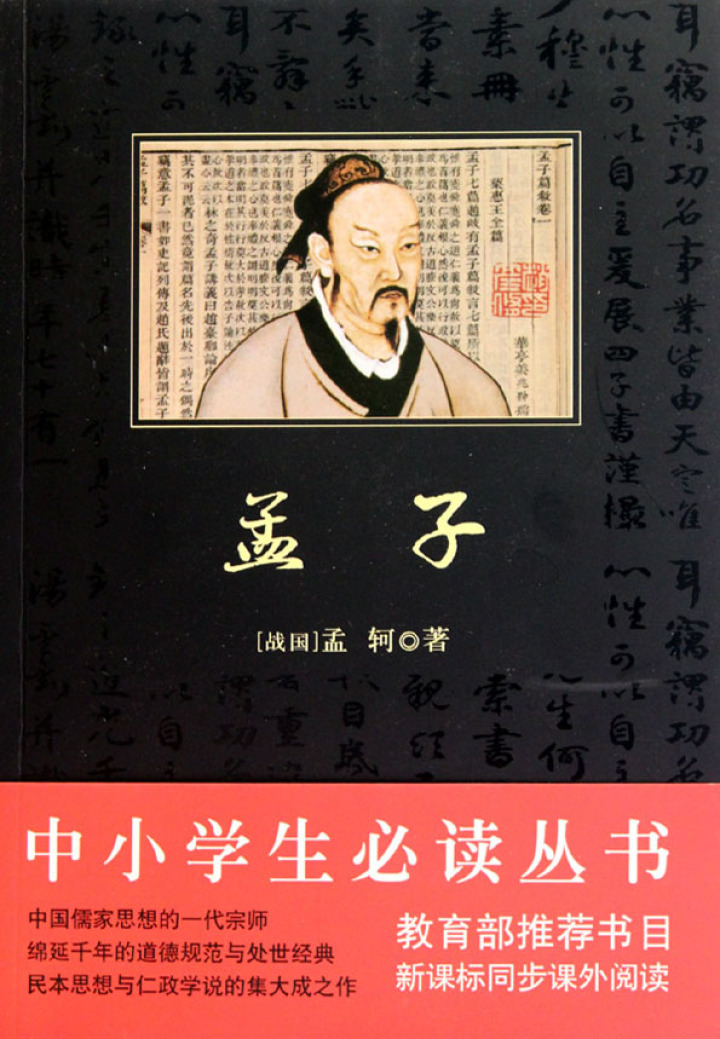
“均”的最佳状态,当然是“天下为公”。儒家赞赏的中庸楷模,都是大同时代“有天下而不与”的人物。因为当时还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私有制尚未产生;而私有制一旦形成,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衡,就会打破所有的平衡。相比“天下为公”的大同时代,儒家其实并不喜欢“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但它明白,大同时代已经远去,全面恢复它,当时已无可能,尽可能多地保留原始农村公社的某些做法,就很不错了。所以,儒家钟情于“井田制”,主张将山林沼泽等公共资源向公众开放。关于“井田制”,在此我们不必纠缠它的具体样式,只需明了儒家心目中的井田制是什么样子即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和哲学思想,然后敢治私事。”这是孟子心目中的井田制,显然它是一种名义上为天子所有、国家调控、生产者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更不能自由买卖的土地制度,保留了原始农村公社的一些特点。董仲舒说:“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可见商鞅变法的实质,在经济方面,就是推行土地私有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这是儒家深恶痛绝的做法,也是儒法斗争的焦点。从反对“初税亩”和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到孟子的“正经界”“分田制禄”、董仲舒的“限民名田”,一直到朱熹在漳州泉州等地半途而废的“正经界”行动,儒家一直寄望国家调控生产资料、遏制私有化和自由买卖导致的土地兼并。为了有效地调控,必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必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必须“一统”。
顺便说一下,儒家这种寄望国家调控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倾向,对我们影响很大,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能接受什么、不能接受什么。
经济利益要适度均衡,政治权利也要如此。“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雍也可使南面”。儒家致力于弘扬大同时代的“明扬侧陋”、“俊乂在官”、“野无遗贤”的政治传统,他们推崇的大舜、大禹、伊尹、傅悦等,出身都很低微。对那些把持权位的世袭贵族,孔子很瞧不起:“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孟子更是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只要德才兼备,不论出身,人人都有为官从政、治国理民的权利。这就是儒家坚持的“政治平等”:承认阶层差异,但反对阶层固化。而且,儒家认为权利与职责是对应的、平衡的,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提法,就是典型的“权利职责平衡说”——君臣父子,各居其位、各享其权、各尽其责。在这一环环相扣的链条上,关键的环节是君(父),他必须正身率下,“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君不敬则臣不忠、父不慈则子不孝,责任是相互的荆培运系统准确地理解儒家思想的哲学原理与原理,不能只要求一方尽责,享其权就得尽其责付其劳。“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儒家看来,劳心的“君子”之所以获得较多的利益,那是因为他们付出了更多更“高级”的劳动;劳力的“小人”得到的报酬较少,因为他们付出的是较少的“低级”劳动。一个正常的社会人,无论从事哪种职业,是“高级”的精神劳动还是“低级”的体力劳动,都必须遵循一个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哪怕是“天子”,也必须做好本职工作。《国语·鲁语》中,公父文伯之母敬姜训诫其子的那番话,充分表达了儒家对社会分工和权责利关系的看法。1581年,荷兰国会在海牙召开会议,代表们宣称:“国王和他的子民之间,有一种默契。那就是双方不仅要履行某些义务,也要承担某些明确的职责。如果任何一方没有遵守这份合约,另一方有权视为和约终止。”两百年后,华盛顿杰佛逊们在《北美独立宣言》中,指责英君没有尽到保护殖民地人民安全的职责,还千方百计损害他们,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要推翻他在殖民地的统治。这不过是“君君臣臣”的“海外版”。
在看待人性这个问题上,儒家表现得十分中允。一方面,儒家认为“民之所以生者,礼为大”——人之所以能像人而非禽兽那样活着,关键在于“礼”强化了他的社会属性,抑制了他的自然属性,兼顾二者达到了某种平衡。不同于强调“自然”、实际上将人的本质归结为动物性的道家,儒家认为人的本质不在于其动物性而在于社会性,《礼记·曲礼》指出:“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孟子指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荀子则称人的关键特点是“能群”。但儒家又不忽视人的本能,“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儒家强调以礼教化、增强人的社会属性,不是要消除“人欲”,而是要适度抑制和导控人的本能;而且它知道礼不是万能的,“人而不仁,如礼何!”
在人与神的关系问题上,儒家认可神的存在和作用,“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它虽然没有创设一个万能的上帝,却也懂得利用鬼神来威慑人。可是,它又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强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在《孔子家语·致思》中,孔子与子贡的那段对话,颇能说明儒家对待鬼神的真实态度:既利用鬼神来使人“慎终追远”,又要防止人“攻乎异端”陷溺其中。
中庸是儒家思想的哲学原理,违反中庸之道,沿着它的逻辑走向极端,“儒家思想”就异化为“儒教”。
以祭祖为例:儒家强调慎终追远,这当然没错。但当祭祖发展成祖先崇拜、当祭司们假托“祖先意志”来禁锢人们的头脑,它就异化为“儒教”,祠堂就成了变相的教堂,那些“族长”——乡村祠堂的大祭司,实质上就成了“政教合一”的土教皇。对这种隐性且不断拓展的宗教化,人们往往浑然不觉,但与那种纯粹的关于“彼岸”的理论相比,这种异化而来的“儒教”在控制人的思想方面更加高效。试想,当“顺”成为孝的首则、“三从四德”成为妇女们的精神裹脚布、甚至舅父都可以决定外甥的命运,这种社会还是世俗社会吗?除了僵化与停滞,它还会有别的结局吗?
事实已经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中庸——平衡与适度原则的重要性;今天,尽管已经普遍接受过唯物辩证法的启迪,我们仍然习惯用它来处理问题,而不会上升到思辨的高度。这表明,在它感性的形式下,蕴含着颠扑不破的真理。当然,不光儒家对中庸情有独钟,亚里士多德也推崇中庸,《圣经》也宣扬所谓“中道”,美国人当初的精神领袖加尔文也要求“离弃毫无节制的欲望,离弃不合中道的奢华”。但是,将中庸上升为至高无上的哲学原则、用作一切行动的指南,相对于其他学派和宗教,儒家的理论自觉无疑是最为充分的。
(作者单位:济宁日报社)
随便看看
- 2024-04-29范明静:佛教精神的独特的“心物观”
- 2024-04-282019年儒家思想和哲学范文生于七十年代的人
- 2024-04-28成绩论文题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浅谈儒家哲学
- 2024-04-27专练四十五“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
- 2024-04-27孔子思想的“五大智慧”
- 2024-04-26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知识点总结——
- 2024-04-26墨学与儒学争鸣的两大学说争鸣
- 2024-04-26新修订高中历史配套教材历史教案Plans历史教案
- 2024-04-26儒家五圣的都有谁,又为何没有一代大儒荀子
- 2024-04-26历史上的今天:孔子的思想家学识渊博
- 2024-04-26儒家经典《论语》: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
- 2024-04-252017年国家公务员考试行测:易学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 2024-04-25中国儒家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由程颢和程颐所创立
- 2024-04-25黄勇:《当代美德伦理:古代儒家的贡献》著东方出版中心2019-10
- 2024-04-25:《四书》是中国人必读的书
- 2024-04-25(李向东)先秦儒家的精神就得了解先秦的历程
- 2024-04-252016教师招聘考试:孔子、孟子以及荀子的教育思想
- 2024-04-25辛克丁:中国古建筑儒家哲学道家哲学与中国哲学筑
- 2024-04-25孔子及其儒家思想黄德初1-6清代佚名彬
- 2024-04-25南怀瑾老师:儒家思想在政治哲学方面的贡献和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