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与爱新觉罗氏的“天崩地解”大变局
明清易代与爱新觉罗氏的“天崩地解”大变局
明清易代,爱新觉罗氏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面对这一“天崩地解”的大变局,作为族群精英的士大夫群体中,有慨然就义者如瞿式耜、有自杀殉节者如刘宗周;有为虎作伥者如洪承畴,有媚虏求荣者如孙之獬;有忍辱偷生者如钱谦益,有遁迹山林者如王夫之,不一而足。
不同于很多人的想象,明季殉国人数乃至占整个士大夫阶层的比例事实上都是历朝之冠,明遗民的存在感与影响力更是空前绝后。在北方边患的刺激下,伴随着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和市井文化的勃兴,明中后期以来汉人族群意识是在不断加强的,鼎革之际的巨变更是在这个基础上掀起了经久不衰的波澜。可以说,明末汉奸形象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恰恰也是得益于此。比如洪承畴被怒斥为“冒牌货”的轶闻,就是在广泛的传播过程中产生了数十个版本,后来又融入民间传说,衍生出《洪母骂畴》《承畯贬兄》等一系列故事。
但与此同时,明末的儒生们也遭遇了一个前所未见的、堪称致命的对手。他们将被迫直面自身最根本的缺陷。
01
进与退:华夷之辨的弹性
华夷之辨,又称“夷夏之辨”“夷夏大防”,是中国古代天下观的关键一环,也是儒家礼仪观的重要体现。它当然不同于近现代的民族主义,不过如果非要用民族主义这个词的话,不妨将其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或者说基于文化认同的民族主义。区分华夏和蛮夷的,不是血统、地缘,而是礼仪文化。就像梁启超在《春秋中国夷狄辨》序中解释的那样,“《春秋》之号夷狄,谓其政俗与其行事。”很多人理解不了春秋里面“夷”“夏”的来回变化,就是把思路局限在血统和地缘上了。
对待异族,孔子固然不认同,但他想的不是消灭、征服或奴役,而是教化,即所谓“有教无类”,“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就是这样的道理:夷狄能遵行华夏的礼仪,就可以被接纳为华夏的一员,反之,中原的诸侯也有可能因“不行礼治”而变成“新夷狄”。
相对而言,基于文化认同的华夷之辨更加包容、开放, 传播能力强,这也是华夏文明能有这么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这种传播能力实际上是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实力之上的。一手握剑,一手持书,是汉唐边吏的标准形象。韦皋能够“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靠的是他对吐蕃战无不胜的威名。与之相应的就是,一旦形势逆转,进攻就会变成退守,“教化”难以实行而代之以“隔离”,文化认同受到质疑,而代之以地域、族类认同,如江统《徙戎论》就认为夷狄“法俗诡异,种类乖殊”,主张“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明中叶以后士人对元渐趋否定,不乏极端言论,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其在与蒙古的冲突中颓势日显。
“变夷”与“攘夷”的此消彼长,可以看做是华夷之辨的“文化弹性”,而到了异族入主中原、华夏文明面临存亡危机的时候,这一“弹性”就“减弱了很多”,乃至走向彻底撕裂:有人选择将“退守”执行的更彻底,比如王夫之的“华夏不自畛以绝夷,则地维裂矣”,夷夏之别在他这里严苛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夷狄已成非人的“异类”,甚至就连河北都被认为是胡化难驯了。有人则另辟蹊径,比如郝经的“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 只要祭拜孔圣,开科取士,似乎就是“用夏变夷”的良好开端了,甚至可以将延续文明、传承圣学的希望寄托于此。当然更多的人是把它当做了一块遮羞布,一个放弃坚守的借口。无论如何,这种理解方式大概是孔孟所始料未及的。
进可攻而退难守,这归根到底是春秋战国的时代背景决定的,《公羊传》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再怎么说也只是夸张的表现手法罢了,所以孟子才会自信地宣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大概先圣们也未曾想到华夏文明居然会落到那样的地步吧。
这种衰落经常被归罪于儒家和所谓的文官集团,其中的错误认知和刻板印象姑且不去谈,至少对本文所关心的那些由明入清的儒生来说,虽然他们中不乏投笔从戎、起兵抗清者,但说到底疆场厮杀并不是他们的责任。或者说,在军事上的失败彻底无可挽回、新朝的统治日渐稳固之后,属于他们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02
表与里:全方位的改造
如今我们回顾这次不流血的交锋,只能用四个字来评价:
节节败退。
很多人喜欢说异族政权总是被汉族同化,这固然不是纯粹无中生有的意淫,但依然带着一股阿Q的味道。世纪之交兴起的新清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汉化”这一叙事的反思。诚然这样的反思是有意义的,不过即便不考虑细节上的争议,我还是更认可何炳棣所说的,“汉文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各自鲜明的特征”,如果汉文化并不曾有过一个固定的核心理念和清晰的边界,那么“非汉”特性又从何谈起呢?无非是另一种建构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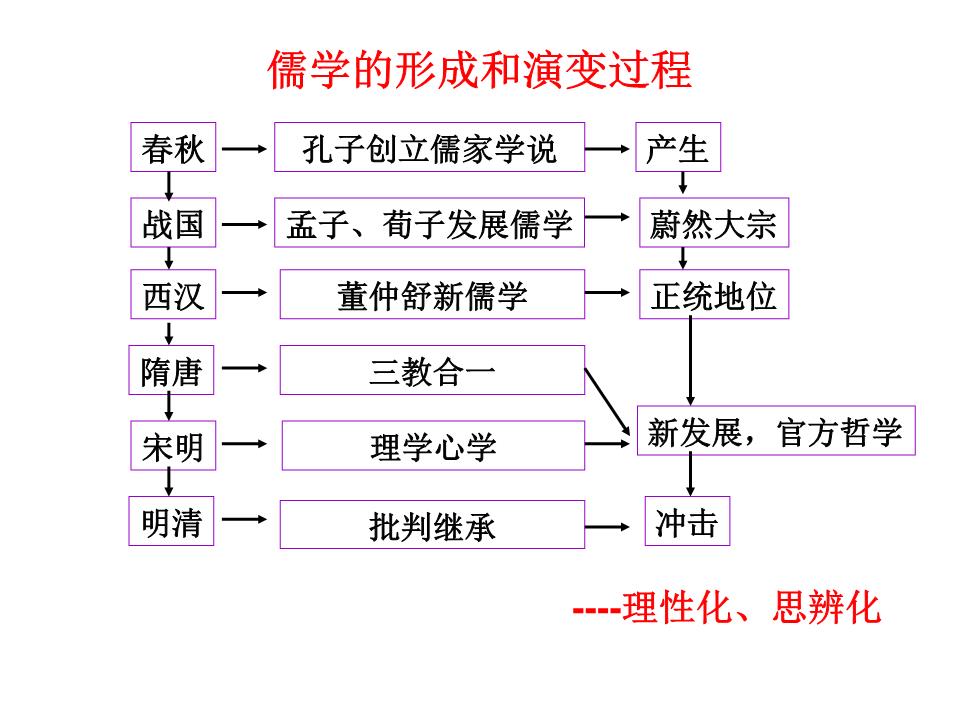
但儒家不同,它是一个宗旨明确的学派,虽然并非万世不易,但也绝不能视为一艘可以无限置换的忒修斯之船——经历了剃发易服的儒生,还能心安理得地面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样的“圣人言”吗?
“陛下平定中原,万事鼎新,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剃发令的颁布固非孙之獬一人之力,但这句话确实道出了统治者的担忧,而他们最终选择用屠刀和剃刀来进行“以夷变夏”。
相比衣冠发式的变化,思想的转向更加隐蔽,但却也更令人惋惜。明中后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从陈白沙到王阳明,心学逐渐打破了理学的统治地位,甚至进一步成为主流,而后以泰州学派为代表的阳明左派日趋激进,开始反对礼教甚至否定孔圣,另一方面,王学末流又走向空谈、流于狂禅和享乐主义,遂有东林学派倡实学而救其蔽,引领了晚明“由虚返实”的思潮。此外,晚明士大夫在与西学的交流中,也产生了“以耶补儒”这样突破性的观点。
而这一演进过程,由于明清易代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葛荣晋《明清实学思潮史》中将明清实学细分为:实体实学(理学本体论的一支)、经世实学、科技实学、启蒙实学和考据实学,然而其中只有考据实学在清代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其余四者在清廷统治日趋稳固、遗民一代渐次凋谢之后,就迅速沉寂下来。
清代朴学(即考据实学)毫无疑问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座高峰,但正所谓“一枝独秀不是春”,各个学术门类之间本应是相辅相成的。《易》有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顾炎武认为“非器则道无所寓自许”,是对晚明以来空疏之学轻视“器”的批评,而非对“道”的否定。他继承并发扬了东林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然“器”易学而“道”难传,清代的政治环境更是几乎没有“道”的生存空间,于是尊奉顾氏为“清学之祖”的乾嘉学者,却大多埋首于故纸,博古而不通今,论史而不议政,连地理这样的学问也不复明季的“征实重用”,而走向了纸上谈兵,实际上又变回到了东林学派所批评的“桎梏于训诂辞章”。
当然,清代绝非只有考据学,但即便只就理学而言,转变也是很明显的。王汎森将其概括为“心性之学的衰微”和“形上玄远之学的没落”,这一变化,“使得宋明儒家思想中的超越性逐渐渺于无形,超越的、理想的、批判的道德形上力量不再具有支配性”,取而代之的是“‘庸言庸行’成为清代思想家所提倡的标准”。
夏明方则将这种变化概括为“清代的帝王儒学或新儒学”,其新“就在于担当这一体系之解释者的‘夷狄’身份”。
不幸的是,很多人对儒学的印象恰恰是基于清代的,比如今天被视为”国学经典“、实则是奴化教育的《弟子规》,是清代秀才李毓秀写的;屠夫曾国藩被奉为“近代圣人”,他的日记和家书则被当做成功学的圣经。因此这种改变,很多时候是难以察觉的,也是难以挽回的。
03
刀与笔:不平等的较量
马克思说过,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永历三年元日(公元1649年2月11日),顾炎武写了一首诗,诗中有一句“正朔虽未同,变夷有一人”,慨然以“变夷”为己任,但讽刺的是,后来这句诗却被改成了“变支有一人”。
清初文字狱之酷烈,可谓空前绝后,“时间之长,案件之多,规模之大,株连之广,花样之翻新,手段之残忍都是没有前例的”,而影响更为深远的,是在这种强大政治压力下产生的“自我压抑”现象,王汎森将之概括为“权力的毛细管作用”。相比之下,载于史册的诸多“大案”,不过是冰山所露出的一角。
每一本查获的“违碍之书”,背后可能有滚滚而下的数十数百人头,但更为普遍的是随之而来的无所不及的自我审查和删篡,上面顾炎武的那句诗,就是他用自己发明的一套名为“韵母代字”的密码所修改的。
从作者、编者到书商、读者,从留白、隐语、张冠李戴到挖改书板、撕去封皮、刊以墨钉, 他们小心翼翼而又绞尽脑汁地规避着禁忌。要知道,当时并不存在一份公开的“禁书名单”,清廷也并不能像老大哥那样无孔不入,这种基于猜测揣度的自我删篡,其实就是在不自觉地传播政治压力、扩大敏感范围。
“寓禁于征”的四库全书,禁毁和删改的古籍数倍于今天所能看到的部分,这也要归功于执行者在政绩压力下挖空心思的捕风捉影。康熙朝的大案大多涉及明清之际史事,雍正朝重点针对的是官员党争,而乾隆时代的文字狱似乎根本没有什么特定的目标,这恰恰是最可怕的——他并不是要消灭某些“敏感词”,而是要建立一个人人自危的环境,非但“批评”是不允许的,“歌颂”同样危险,连以“忠臣”为期许都有可能触怒皇帝。最安全的方式,莫过于将书本付之一炬,从此闭口不谈时事,也不去写什么日记。
统治者的手段当然不是限于“破坏”。
严迪昌《清诗史》中提到,“在中国诗史上从未有像清王朝那样,以皇权之力全面介入对诗歌领域的热衷和制控的”,康熙通过与翰林词臣的诗歌往来,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初诗歌的走向,更借此营造出一种“亲贤”的“圣君”姿态。
而对于充当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学,统治者的态度则是不加掩饰、简单粗暴的控制和利用。康熙三十三年,皇帝针对翰林官员举办了一场名为“理学真伪论”的考试,康熙自己做考官,翰林官员当考生,对包括帝师熊赐履在内的诸多名儒进行了毫不留情的羞辱和讽刺:“昔熊赐履在时,自谓得道统之传······今又有自谓得道统之传者,彼此纷争,与市井之人何异?”何为真理学,皇帝一言可决,臣子只需“身体力行”而已。
就连被一些儒生视为“行中国之道”的科举,也是经过了统治者的改造的。本杰明·艾尔曼曾专文谈论过“清初考试中自然之学的排除”,认为传统儒学是能够实现对“自然之学”的包容的,因为“这些是礼仪正统的组成部分”。科举考试中关于自然研究的策问就体现了这一点,但到了清代就极为罕见了,因为清初统治者出于合法性的考虑,禁止了天文历法、乐律和计算方法等方面的内容。
如果说文字狱是刀对笔的杀戮,那么所谓的怀柔,无非就是伪装成笔的刀和被摧残的笔之间的不平等的较量——否则,“聪明天纵”的康熙,怎么不去找几位遗民大儒来辩一辩义理,只敢对翰林词臣大发威风呢?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弟子规》式伪儒学的出现,就不是什么难以想象的事情了。
04
君与师:儒家路线的根本矛盾
孟子曰: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除了敌人的强大和凶残之外,儒家自身的问题更加不容忽视。
实际上,这种来自统治者的压力,本来就不是清朝才有的。秦有焚书坑儒,汉有党锢之祸,明有禁毁书院,甚至科举制度本身,就可以看做是朝廷对知识分子的一种驯化手段。所以余英时会说,“中国历史上向来就有两个‘儒家',一个是被迫害的儒家,一个是迫害人的儒家”。
这种区分固然有道理,但并不意味着此二者应该是完全割裂甚至对立的。只强调统治者的利用和篡改,或是不肖俗儒的误读和曲解,甚至将他们“开除儒籍”,归根结底无非都是“诉诸纯洁”式的辩护手段,不足以真正地解决问题。
作为一个高度入世的学派,儒家始终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借用《庄子》的术语,是“内圣”与“外王”的矛盾,按照宋儒的表述,是“道统”与“治统”的矛盾,是“师道”与“君道”的矛盾。
然而,即便是那些以“道统”自任的一代宗师,也并没有设想过与“治统”分庭抗礼,遑论取而代之了明清之际的儒家思想和欧洲启蒙思想的不同,“治教合一”“作之君、作之师”才是他们所憧憬的理想政治模式。诚然,很多儒家士大夫会以较高的道德标准去批评朝政乃至于皇帝本人,但归根到底这仍然是在对后者做“致君尧舜”的加法,而非做“限制皇权”的减法。所以,只要皇帝的脸皮够厚,就可以轻松地将这一套理论据为己用。
无怪乎有人会觉得,异族才是最适合儒家理论的完美统治者。也只有在这种时候,“君臣大义”与“夷夏之分”孰重孰轻才赤裸裸地摆到所有人面前,成了一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对此,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明言“不以一时君臣之义,废古今夷夏之通义”,吕留良也针对《论语》中“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一句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事者。”不过这样的立场恐怕只能说坚定有余,突破不足,仍然在很大程度上维护着“君道”。《大义觉迷录》中所呈现的曾静之幡然悔悟或许别有内情,但雍正的驳斥至少看起来是抓住了其自相矛盾之处,也证明了一点:不彻底摆脱“君道”的束缚,是不可能真正维护“华夷之分”的。
孔子曾经曰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实则某种程度上来说,“君”与“夷”可谓是是同类。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的第一篇《原君》中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也在未刊的《封建》一篇中感叹“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都曾引起后世学者的重视,但如果将两句话联系起来看,又会别有一番境界。王夫之还曾将“中国、夷狄”之大防”归结为“义利之分”,那么“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的人君,岂非比他所批判的商贾更接近夷狄么?
相应的,“师”理当是“华”的核心代表,诸夏可以无君而不可以无师。上则以道化君,下则以礼导民明清之际的儒家思想和欧洲启蒙思想的不同,外则宣播声教,内则传承圣学,本都是儒家师者的职责,但事实上他们的承担却并不能算是非常积极,较之西人的传教热情,更是相去甚远,而“上”与“外”两个方向尤其如此。当然,这很大程度上是严酷的现实条件所导致的。无论如何,在“治出于二”的时代,“师”既然做不到将君主培养成圣贤,又如何能够“用夏变夷”呢?既然常常不得不向“君”屈服,那么“变于夷”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君”与“夷”的合体,带来了空前的大一统与臻至巅峰的专制王朝,最终却也导致了二者的同步消亡。而随着“民国”到来明清之际的儒家思想和欧洲启蒙思想的不同,“师道”的自我期许逐渐与启蒙意识结合了起来明清易代与爱新觉罗氏的“天崩地解”大变局,“华夏”的文化认同则蜕变成了“中华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看起来,历史似乎还是挺公平的。
05
余论
时过境迁之后,明清易代的这段历史又经历了多次重新建构与解读:有的格外强调其中的种族因素以及“华夷之辨”与民族主义的同质性,有的喜欢挖掘遗民学者身上的民权、自治等启蒙要素,还有的干脆将“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打扮成爱国主义教育名言。这些解读都未免刻意于靠拢近代传入的西方理念和思维了,但反过来,如果一味强调“古代”族群意识不彰、“华夷之辨”只是少数迂腐文人的无谓坚持,以及儒家学者泥古不化所以不可能有实质性的突破,则又显得过于决定论乃至欧洲中心主义了。
实际上,要想认识到顾、黄、王等人思想的价值,并不需要像梁启超那样借助卢梭、斯密这些西方思想家作为标尺;而王家范所批评的“倒回去”的思路明清易代与爱新觉罗氏的“天崩地解”大变局,本身就是突破所在:无论是夷夏之分还是君臣之伦、义利之辨,明末学者在面对那样一个空前的“完全体”敌人时,正是以这种方式回顾两千年的“天下一家”历史,将诸多儒学命题的批判力度推向了极限。纵然这一极限并没有对历史有决定性的影响,也未必能让执着于进步史观的今人满意,但它仍然是有意义的。
随便看看
- 2024-05-18儒家文化的“礼”儒学的真谛是仁礼一体
- 2024-05-17儒家经典:四书里的《论语》,四书泛舟,人间清欢
- 2024-05-15安徽三祖禅寺住持上宽下容大和尚出席旃檀禅林讲堂
- 2024-05-15道家思想经典语录,儒家、道家、佛家思想对比,经典好文!
- 2024-05-14(知识点)中国古代的思想与科技第一课
- 2024-05-14(每日一题)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16页珍藏版)
- 2024-05-13高中历史必修三必备知识结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2024-05-11礼教与儒家传统的认知及想象主导着这场批判
- 2024-05-09明清思想转型暨纪念顾炎武诞辰4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江苏举行
- 2024-05-09儒家智慧梁涛 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七月廿八日壬寅耶稣
- 2024-05-08:中国文化何以有某些特点
- 2024-05-08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倪培民谈天地为己为人为天下
- 2024-05-082016下半年教师资格考试备考:明清之际进步思想
- 2024-05-08儒家人文思想暨第三届国际青年儒学论坛成功举办
- 2024-05-08高中历史必修三第一单元《中国古代传统主流思想的演变》
- 2024-05-07:先秦儒家和其他诸子百家对中国的影响
- 2024-05-07(每日一题)明清之际的儒家思想——宋明理学
- 2024-05-06儒家文化对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在于其道德价值,教育价值和政治价值三方面
- 2024-05-06中华三千年文明史上的很多东西,我们现在盖楼还用木制榫卯吗?
- 2024-05-05儒家的人生智慧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是对人生关注与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