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悦笛有学者:生活美学为何在新世纪得以全面出场?
刘悦笛有学者:生活美学为何在新世纪得以全面出场?
余开亮
“生生”是中国哲学精神所在,包含着生命、生成、生活、生化等诸多意蕴,代表了中国文化对天、地、人存在状态的一种基本看法。本专题刊出的有关生活美学、生态美学及其关系的三篇文章,虽立论有别,但皆以关注“美好生活”为旨趣,体现了中国当代美学理论建构中一种融通古今的学术视野。
为生活立“美之心”
刘悦笛
有学者认为生活美学的提出是20世纪中国美学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的中国美学刘悦笛有学者:生活美学为何在新世纪得以全面出场?,从对西方超功利美学的引进开始、到美学大讨论中对人的实践的讨论、再到生活美学的兴起,这一美学史的发展表明美学在不断向具体的、活着的、小写的人落实和生成。从美学史角度对生活美学的这个历史定位,笔者基本赞成余开亮儒家的生态智慧与美好家园建设,那么,生活美学为何在新世纪得以全面出场呢?
时代境遇:以“美生活”来提升“好生活”
当今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变迁,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构成了生活美学得以兴起的历史背景。我们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应该包括两个维度:一个就是“好生活”,另一个则是“美生活”。好的生活是美的生活的现实基础,美的生活则为好的生活的升华。好的生活无疑就是有“质量”的生活,而美的生活则是有“品质”的生活。
生活美学就是要以“美生活”来提升“好生活”,以有品质的生活来升华有质量的生活,并对人民大众进行生活美育的普及。生活美育则是生活美学的逻辑推演,生活美学通过生活美育得以落实。如今,越来越多的从事茶道、花道、香道、汉服复兴、工艺民艺、非遗保护、游戏动漫、社区规划等领域工作的人士,都积极融入生活美学的潮流中,并在各地传播着美学美育观念。
实际上,“生活美学”,不仅是一种关乎“审美生活”之学,而且更是一种追求“美好生活”的幸福之道。前者之“学”是理论的,后者之“道”则是践行的,二者恰要合一,这就是美学上的知行合一。
整个东方美学,从根源上也是一种“生活美学”。东方美学不仅是可“知悟”到的人生智慧,更是诉诸“践行”的现世传统。这是由于,西方美学曾经更关注艺术,东方美学却早已聚焦生活。有趣的是,“东方美学”这个词却不是东方人提出的,法国历史学家雷纳·格鲁塞在1948年《从希腊到中国》中最早用过,而后才有东方对自身美学传统的“自觉意识”。由此,也形成了最初的“比较意识”,一说“中国美学重‘形’,日本美学重‘色’,而韩国美学重‘线’”。但实际上,真正连纵起整个东方美学的内核乃为“生活”,它们皆为一种倡导生活化的“生活美学”。
东方生活美学关注审美与生活之间所具有的“不即不离”亲密关系,注重在日常生活中体味生活本身的美感。中国的“生活美学”就可以代表东方传统,这种传统就是一种始终未断裂的生活传统。中国古典美学作为最“原生态”的生活审美化传统,形成了一种忧乐圆融的中国人的生活艺术。
生活美学:审美与生活不即不离
审美与生活的不即不离,就是一种既不接近亦不疏远的关联。中国生活美学,就是强调审美与生活之间如此的关联,这里的“生活”,乃是中国人自己的“生活”;这里的“美学”,也是中国化的“美学”。
生活乃是“生”与“活”的合一,生与活有别,生只是生物性的,动植物均有生,但只有人才能活。每个人都要“生”,皆在“活”。在汉语的语境里面,“生”原初指出生、生命以及生生不息,终极则指生命力与生命精神,但根基仍是“生存”。“活”则指生命的状态,原意为活泼泼地,最终指向了有趣味、有境界的“存在”。明末清初著名画家石涛所说“因人操此蒙养生活之权”当中的“生活”,正是此义。中国人所理解与践行之“生活”,所言说的就是鸢飞鱼跃那般的存在,有着鲜活的内涵与践履途径。
人们不仅要“过”生活,要“活着”,而且要“享受”生活,要“生存”。按照法国哲人列维纳斯的主张,在西方世界,对古人来说,存在指的是“事物”;对现代人来说,存在指的是“最内在的主体性”;对当今的人们来说,存在指的则是“生活”,也就是一种与自身、与事物的直接私密关系。在此意义上,中国人其实早就参透了生活的价值,由古至今都生活在同一个现世的“生活世界”当中,而不执于此岸与彼岸之分殊,这就是中国人的大智慧。
人们不仅过日子,而且还在“经验”着他们的生活,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是始终不离于感性的。列维纳斯还说过,所有的享受都是“生存的方式”,但与此同时,也是一种“感性”存在。“美学”这个词原本就是感性的意思,美学作为学科之本意就是“感性学”。但在中国,却将“感”学之维度拓展开来,从而将之上升到“觉学”之境,而这“感”与“觉”两面恰构成“不即不离”之微妙关联。因此,中国的“美学”,就不仅是西学的感性之学,而且更是一种感性之智。
“生活美学”之所以指向了“幸福”的生活,是因为,过生活就是享有生活,并去寻求生活的幸福与幸福的生活。幸福本身,就是一个美学问题,而非伦理问题。由古至今的中国人,皆善于从生活的各个层级当中来发现“生活之美”,去享受“生活之乐”。中国人的生活智慧,就在于将“过生活”过成了“享有生活”。也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美学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得以生长,它本然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
在这个意义上,生活美学(抑或东方生活美学)不囿于西方的感性之学,而更是感性之智,美学恰恰关乎“幸福”的追求余开亮儒家的生态智慧与美好家园建设,并致力于让人们的生活过得美好。“生活美学”恰是一种研究幸福之学,也是一种实现幸福之道!
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的基本面向
既然中国古典美学从本源上说就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美学,在这个根基之上,中国美学可以为当今的全球美学贡献出巨大的力量,因为我们的“美学传统”就是生活的,我们的“生活传统”也是审美的。我们当代的“生活美学”建构也需以中国古典美学为根基,形成一种古与今的“视界融合”。
“生活美学”中蕴含着华夏传统的生命意识、生活观念和人生追求脉络:一方面本然呈现出摇曳生姿的古典生活现场之美,另一方面又指向了其来路、走向和转化的可能性。这就需要当今中国的美学研究者,一方面积极地参与到与国际美学界的最新交流当中,另一方面又回到本土去挖掘中国古典“生活美学”的资源。
中国古典生活美学涵摄了“自然化”(性)、“情感化”(情)和“文化化”(文)三个基本的维度,这就非常全面地覆盖了从生理的、情感的到文化的诸种生活,其基本问题意识便是探讨如何实现审美化的生活,由此生成一种忧乐圆融的生活传统。这里的美学就不再是聚焦艺术的“小美学”,而是融入生活的“大美学”。
“大美学”主张让美学真正回归到其得以自然生长的生活大地之中。当我们在找回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传统时,就是要为中国人的生活立“美之心”。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可以分为十个基本面向:天气时移的“天之美”、鉴人貌态的“人之美”、地缘万物的“地之美”、饮馔品味的“食之美”、长物闲赏的“物之美”、幽居雅集的“居之美”、山水悠游的“游之美”、文人雅趣的“文之美”、修身养气的“德之美”和天命修道的“性之美”。通过天、人、地、食、物、居、游、文、德、性这十个方面,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大智慧可以被深描出来。这些生活审美化的传统,其实都是“活着的”传统。中国文化传统之所以延续至今,乃由于生活的传统从未中断,审美的传统从未中断。“生活美学”就是这未断裂传统中的精髓所在,或者说,就是这传统之“感”与“觉”的精髓。
中国既是“礼仪之邦”,也是“美善之国”。生活美学也必然在承继“礼乐相济”的华夏悠久传统中扮演重要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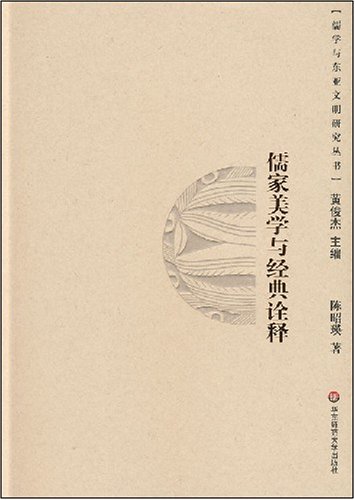
生态美学: 迈向生态文明的美学转型
程相占
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极大地影响并改变着地球生态系统,导致这个系统的稳定与平衡被扰乱,一系列生态灾害严重威胁着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生命。正是为了拯救生态危机,为了地球生命共同体的可持续存在和健康发展,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人类社会开始了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深刻反思,并逐渐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生态美学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兴起的美学研究新形态,代表着美学的发展方向,可以简单地视为美学的生态转型。
一
一般认为,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的标志是1750年德国美学家鲍姆加登公开出版《美学》一书。那个时候既没有严重的生态危机,也没有作为独立科学的生态学。因此,现代美学既不可能考虑生态问题,也不可能从生态学借鉴理论资源。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生态学远远超越了其原来所属的生物学领域并对人文学科各个领域都产生着重大影响。可以说,几乎所有人文学科都正在发生着程度不等的生态转型。美学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美学也正成为生态文明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反思现代美学的根本缺陷,实现美学的生态转型,是生态美学研究的基本思路。
西方现代思想在界定人之为人时,通常将人视为具有心灵、能够思维的主体;人的存在的特征,突出体现为既与身体无关、又与环境无关的主体性。这种哲学观念体现在美学上,就是以康德为代表的主体性美学:主体运用其心灵的先验能力构建表象,当心灵中的表象与主体的感受及其情感发生关联的时候,主体就根据其感受的愉悦与否作出审美判断,将能引发愉悦的表象判断为美的,反之则判断为丑的。在围绕主体展开的审美判断中,客体基本上被忽视了;康德甚至特别强调,为了确保审美的纯粹性,必须忽略客体及其实在性。按照这种美学思路,主体被极度高扬了,客体则被极度贬低了。以自然为代表的客体,仅仅是主体构建心灵表象的原材料;自然不但没有任何主体性,而且没有任何内在价值或内在目的。简言之,现代主体性美学通过高扬主体性及其创造力,将人类这个物种从自然世界中无以复加地突出出来,甚至割断了人与自然界的血肉联系。
二
针对上述理论弊端,生态美学首先根据生态学原理,将人类的存在理解为“生态存在”,也就是身在生态系统之中的存在:生态系统在其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孕育了包括人类在内的众多物种,是人类存在的母体;离开这个母体,人类就不可能生存,更不可能发展。人类是生态系统生生之功能、生生之德性的具体体现之一。人类之所以被称为“天地之心”“万物之灵”,是因为人能够凭借自己的天赋良知及其反思能力,将自身对于生态系统的责任理解为“参赞天地之化育”,将自身使命理解为帮助生态系统达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理想共生状态。按照生态美学的思路,自然不是人类可以无度利用的资源,而是人类得以产生且赖以生存的本源。生态美学从生态存在论出发,其核心命题是,自然事物以人类的审美知觉为通道,如其本然地显现其自身。这一核心命题可以概括为:美者自美,因人而显;生态审美,生生不息。
正是从生态系统的生生特性出发,生态美学展开了对于审美价值的生态重估,探讨审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辩证关系。在生态美学之前的美学理论中,“美”与“审美”都是极其光辉灿烂的字词,审美价值毋庸置疑地居于价值序列之首。但是,从生态审美的高度来看,生态美学的理论思考多了一个重要参照,即生态健康,也就是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平衡。生态学研究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生态美学则研究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审美互动,清醒而自觉地考察人类审美活动对于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严肃地反思和批判审美活动对于环境的破坏。生态美学看到,人们通常只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来判断一个事物的美丑,通常将审美愉悦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很少考虑审美偏好的生态后果,因而造成了对于环境的极大破坏。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人们通常喜欢整整齐齐的草坪,通常用“杂草丛生”来贬低一个地方的审美价值;然而,草坪的维护需要消耗大量的水和化肥,对于淡水资源奇缺的地区来说,草坪审美偏好却成了生态破坏的重要诱因。又如,人们在长期的审美活动中,逐渐形成了对于特定植物的习惯性审美偏好,通常只运用特定的植物来创造景观;这样的植物审美偏好,既造成了植物景观同质化单一化,又对于植物多样性产生了不良影响。简言之,生态美学在认真反思形成人类审美偏好的社会、历史、文化根源的基础上,以生态健康为价值标准,将事物的生态价值放在审美价值之前,通过探讨审美偏好与生态灾难之间的关系,反思和批判人类审美偏好的生态后果,努力倡导一种有利于生态健康的生态审美观,从而使美学在拯救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三
生态美学也引发了艺术观念的生态转型。艺术与自然的关系一直是美学理论的核心问题,艺术曾经长期占据美学研究的中心地位,黑格尔甚至将美学视为艺术哲学,同时认为艺术美高于自然美。现代美学从其主体性思路出发,通常高扬艺术家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进而用表现论来解释艺术现象,将艺术视为艺术家表达情感世界的自由创造。根据这种艺术哲学,自然仅仅是艺术家用来创造艺术品的原材料,其逻辑与现代工业生产完全一致:自然事物可以由人类随意加工和改造。与此相反,生态艺术美学则认为,自然自身有着远为人类所不及的巨大活力与创造力,天才的艺术家无非是自然之子,其艺术创造活动无非是一个“代自然立言”的过程,无言的自然通过艺术家的“代言”活动而表达其自身的内在价值与内在目的。
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内外的生态美学研究已经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理论成果。生态美学以生态学为理论范式,将人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审美互动作为理论基点,将人类的审美偏好及其生态后果作为重要的理论命题,站在是否有利于生态系统之稳定与平衡的高度,探讨审美价值、审美满足与生态健康之间的矛盾及其化解之道,其核心主张是承认自然的优先性,努力将审美愉悦与生态关怀统一起来。这种形态的美学理论不但有助于反思和批判现代美学的根本缺陷,而且有助于引导人们逐步形成一种有利于生态健康的生态审美观,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儒家的生态智慧与美好家园建设
余开亮
生态美学以建设世界万物宜居、美好的生存家园为研究出发点,以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环境整体为研究对象,倡导一种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和谐与生命互动。在生态美学看来,自然存在的环境本身就具有“全美”价值,而实现人与自然生态的平衡与连续性就是美,反之就是丑。所以,人类的活动既不应以自我中心为原则来实现对自然环境的无休止掠夺,也不应以主观审美趣味来随意破坏、改造自然,而应在尊重自然环境的存在价值基础上,遵守自然生态规律来进行活动。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极为注重天时、地利、人和的息息相通,休戚与共,有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一

荀子云:“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在儒家哲学中往往是以“天”或“天地”观念来进行阐发的。“天”在儒家哲学中具有多重意义,如冯友兰曾把中国哲学中的“天”分为物质之天、主宰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等诸义。不过,中国先秦哲学的一个转变即在于对主宰之天、命运之天进行了哲理化,把“天”与最高本体——“道”结合,形成了以自然之天与义理之天相贯通的天道观。“天道观”的出现表明了一种理性精神的确立,意味着中国哲学从先秦开始就主要是以一种哲学智慧而非宗教信仰的方式来把握内在生命与外在生存环境的连续性体验。要求人去敬守天道、遵循天道而不是去僭越天道、乖违天道,这意味着古人是以自觉的理论反思意识来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
孔子云:“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居处恭余开亮儒家的生态智慧与美好家园建设,执事敬,与人忠。”孔子一方面把“天”视为了万物生命所出的根源,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人应当对“天”有着一种敬畏的态度。儒家天道观中所涵摄的自然之天与道德义理之天的融通,将生态伦理、道德意识渗入对天地自然的认知当中。这就表明,中国古代儒家哲学的“天”或“天地”除了今天的自然界意义外,还赋予了“天地”一种至诚悠远、博厚高明的精神含义。在儒家看来,正是有了“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的至上良善,自然万物才得以获得自身的存在。这种精神含义是与古人所共识的万物同出于天道生成的天人一体观念紧密关联的,因而是精神反思性的,是道德律令式的。儒家对“天地”的这一极具独特性的看法表明,古人虽不是以宗教信仰的方式来把握“天地”,但又始终怀有一颗对“天地”的敬畏珍重之心,从而赋予了“天地”一种神圣性功能。
二
“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天地”这种神圣性功能使得人在自然环境面前能保持谦卑恭敬的姿态,以感恩天地馈赠衣食的心态来面对自然。后世儒者与帝王都是在这种对“天”的敬畏中进行着各种祭祀天地的礼仪活动。“以天地为本”“参赞天地之化育”“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民胞物与”等观念都成为儒家谋求天人合一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活动的指导原则。“天地合而后万物兴。”在儒家看来,只有在与天地万物、外在环境相亲相爱的关系中,包括人自身在内的万物生命才能得到繁荣昌盛。今天生态危机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就是人类对自然资源、自然环境毫无敬畏之心,肆意攫取与过度开发,从而破坏了天地自身的平衡稳定与和合创生。“敬则不逐物,亦不遗物。”所以,重提儒家对天地万物、对自然环境的敬畏之心,对营造美好家园、美好生态环境是极有意义的。
对天地万物的敬畏与尊重,就是要具体落实人与天地万物休戚与共、荣辱一体的观念。在儒家思想中,存在着大量的关于尊重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策略。孔子倡导仁学,他不但要求人与人之间要相亲相爱,而且也要人对天地万物充满仁心。《论语·述而》载:“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说的就是孔子钓鱼但不用网罟捕鱼,孔子打猎但不射归巢之鸟。孔子对待自然万物的态度与焚林而田、竭泽而渔的掠夺心态是截然不同的。《孟子·梁惠王上》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时”,即万物生长的自然时节。“不违农时”“斧斤以时入山林”都表明了对自然万物的利用要尊重客观规律,推行“时禁”。“数罟”,即细密的渔网。不用细网捕鱼,目的是为了保留下尚未长大的鱼与鱼种,这也体现了一种可持续的生态观念。《荀子·王制》则对孔孟的这种生态保护观念进行了更详细的阐发:“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在这里表达的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的生态观念无疑在今天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三
当然,儒家在生态智慧方面作出系统的理论总结的当属《礼记·月令》了。《月令》作为朝廷礼制与国家律令的一部分,概述了天子一年四季的政治活动。作为古人对农耕社会生产与生活管理经验的总结,《月令》中蕴含了丰富的生态保护、营造美好家园的生态美学思想。就基本思想而言,《月令》要求人的活动充分尊重包括植物、动物和土地等在内的自然万物的生长、变化规律,因时而动的保护与利用各种资源。《月令》特别强调,春夏两季是万物生长季节,人的活动更是要以积极主动的行为来保护自然资源,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对于山林川泽土地等资源,《月令》提出在春夏时季要采取多项措施来保护、休养生息这些基础性资源,如禁止伐木、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毋有坏堕、毋起土功、毋伐大树、入山行木、烧薙行水、杀草、粪田畴、美土疆等。对于动物资源,《月令》也提出了在春夏时季的多项尊重动物生长规律的保护方案,如牺牲毋用牝,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麛、卵,毋田猎,游牝别群、则絷腾驹,班马政等。古人的“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的这些认识与实践刘悦笛有学者:生活美学为何在新世纪得以全面出场?,无疑是非常具体而深刻的。
人类现代文明是经由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的推动造就的。现代文明在给人类带来极大便利与生活质量提升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严峻的生态危机。随着全球人口的剧增、城市的蔓延与消费的膨胀,人类过度地利用自然资源和破坏环境来满足自身的发展。因此,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被打破,各种生态危机也接踵而至。而中国儒家文化关于“以天地为本”的生态道德意识、关于“时禁”的生态伦理规范、关于“休养生息”的生态修复观念都有助于实现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
随便看看
- 2024-04-19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 2024-04-15近读王振复新著《南北朝佛教美学史》
- 2024-04-12中国古代哲学哲学道自然审美艺术与哲学的自觉联系
- 2024-04-08中国传统哲学生态观的基本内容和特性有哪些?
- 2024-04-05(每日一题)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规范
- 2024-04-05中国生态哲学思想的逻辑起点——Thisworkisunder
- 2024-04-03知微·行远|友邦堂:幽默风趣的人生态度
- 2024-03-29道家哲学对中国画的审美影响以及在构图中的体现
- 2024-03-05《王蔚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之人类的相处之道
- 2024-02-29中国当代四大美学流派第一种:客观事物美不美全在于主体的主观感受
- 2024-02-17“新一代汇企行”走进创维——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生态建设企业交流会
- 2024-02-14稻田生态的一个侧面——良渚稻田中的石镞
- 2024-02-07中国哲学的“天”与“道”结合
- 2024-02-06余开亮《儒家的生态智慧与美好家园建设》阅读训练及答案
- 2024-02-06百校联盟2020届高考复习全程精练·模拟卷语文注意事项
- 2024-02-06余开亮儒家的生态智慧阅读答案 2015年吉林省四平市高三下学期语文4月月考试卷
- 2024-02-04从天人合一的环境之美、和谐统一的建筑美学
- 2024-01-292020年我州持续抓好农业稳产保供和农民持续增收
- 2024-01-29是写论文用吗?古琴美学中的儒道佛思想
- 2024-01-29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