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弘一法师出世、谢世的文学品性辨正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信誉作者”、吉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王树海先生,于2024年3月28日凌晨3时55分因病逝世,享年74岁。
树海先生宽宏大气,智慧雄放;学术兴趣广泛,多有建树,尤其是在古典文学与佛禅文学领域功力精深,禅魄诗魂,超然远诣。老人家生前十分关心《学报》的高质量发展,曾八次亲赐大作,谨择数文,以示永远的忆念。其八曰:《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弘一法师出世、谢世的文学品性辨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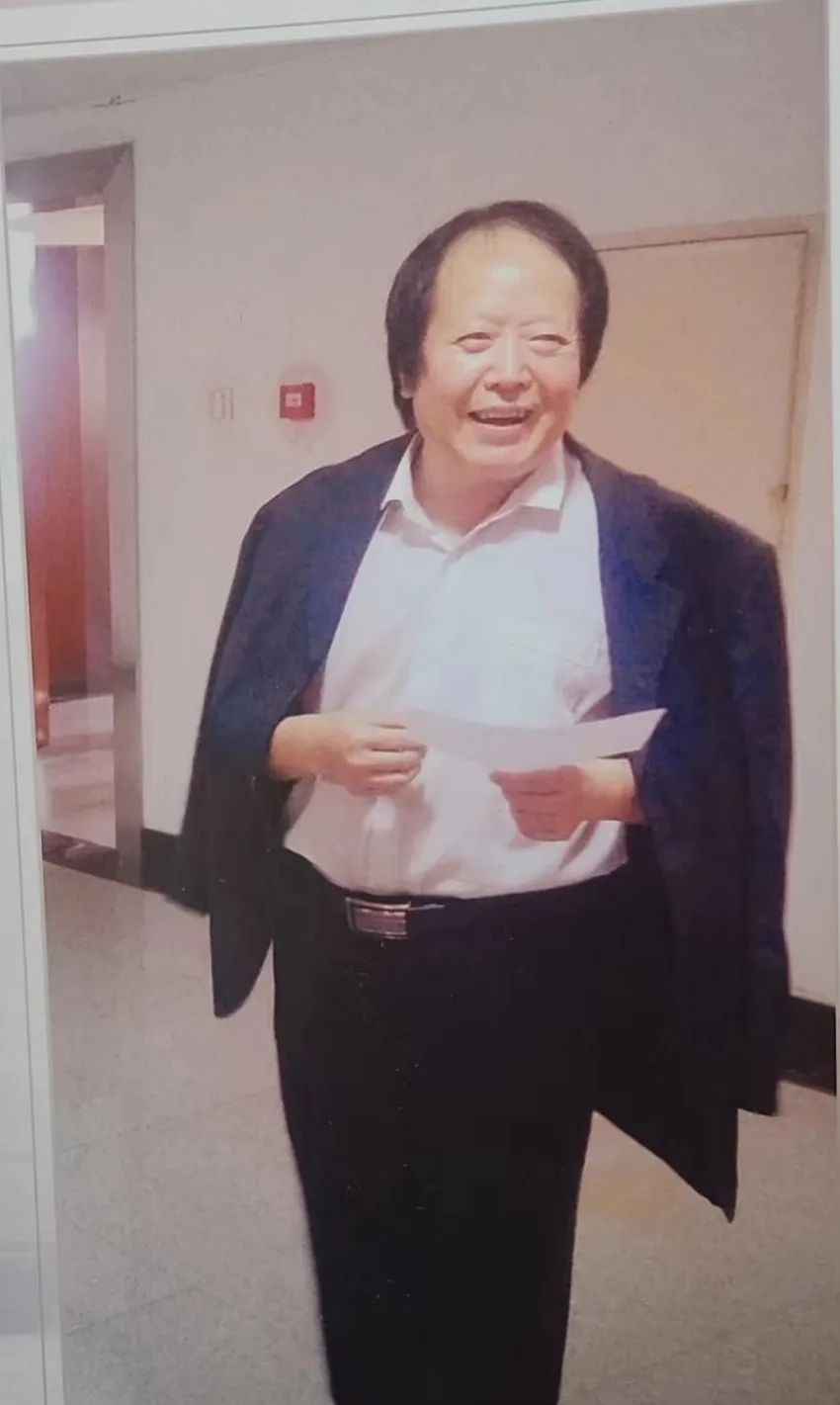
本文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5期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弘一法师出世、谢世的文学品性辨正
王树海 肖菲 | 文
[摘要]背负文学盛名的李叔同,踏进释门后,成为淄素共仰的高僧大德。此间文学进阶的深浅一直牵动着广大读者、偌多信众。法师佛门文学物事,似少专门肃整的研究。教人欣喜的是,出世的法师仍是诗家意气、诗家做派、诗家风范,“有情”宛在。法师“以戒为师”的行持,更趣近文学艺术的同情,“心比平时灵敏,颇有文思”,且“妙思泉涌”,可“信手挥写”。文学爱惜生命,回护朴初,同情卑弱,右袒不幸的根本属性,因生活中的自戒自律而得以保障。法师诠解佛教非迷信、非宗教、非哲学,“独未”说其非艺术,甚至迳称“佛门生活,就是艺术的生活”。释门24年的文学追询达到痴迷之境,之于文学艺术的生命价值,亦悟到“随时新”的命意,当法师“悲欣交集”时际,留给后人的是生的鼓舞,这安详宁静的力量,默如雷霆。同时刻的文学传达:“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是令人期待既久的文学胜境。
[关键词]弘一法师;出世;文学品性;有情;以戒为师;随时新
背负文学盛名的李叔同,1918年8月19日决然放置尘缘遁入空门,成为声名大振的弘一法师。弘一法师(1880—1942),祖籍浙江平湖,俗姓李,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叔同为字,号漱筒佛家的智慧三境是什么意思,别号息霜;工诗词,擅丹青,通音律,精金石,又是早期话剧活动家、艺术教育家;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后专治律藏,其间与丰子恺合作《护生画集》传世。24年的梵林行脚之于他的文学生产是增益抑或减损,尤耐寻味,颇须研究。笔者拟从出世后修持历程和谢世前精神乃至灵魂的呈示状态等方面探讨其与文学的诸多关联,考稽成为“我佛弟子”后的弘一法师其文学成就究竟有多大,文学进阶到底深有几许,藉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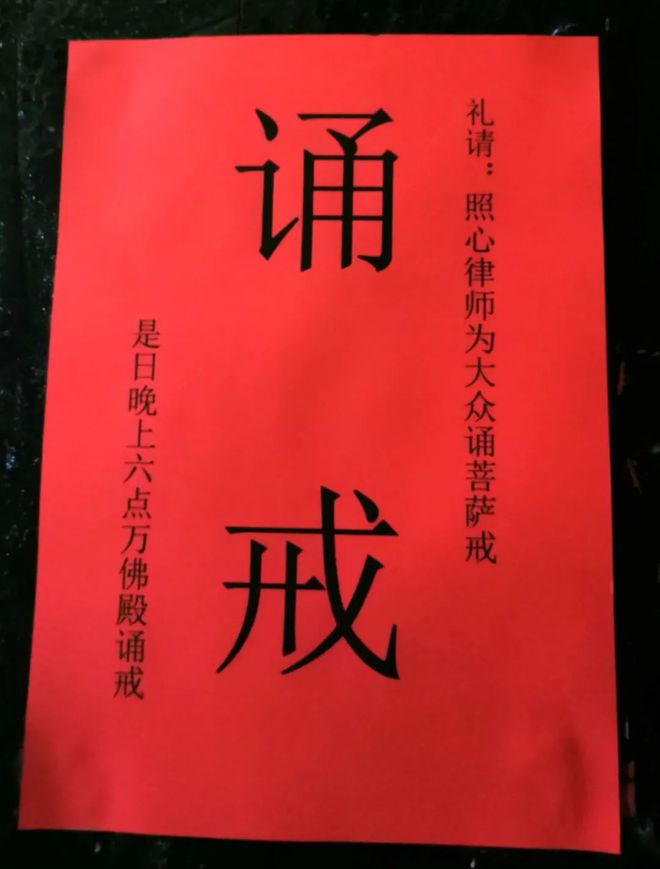
一、进入佛门后的文学风范
弘一法师出家时已是享誉海内外的文学艺术大家,“二十文章惊海内”,亦有诗证:“李也文名大如斗,等身著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李贞)。仅以诗词论,李所创作的《前尘》《感时》《月》《朝阳》《晚钟》《春游》《早秋》《送别》《金缕曲·赠歌郎金娃娃》《喝火令·哀国民之心死》《满江红·民国肇造志感》等等,均不失为传世之作。然而卓有成效、多所建树的他却陡然挥手前尘,放掷万缘,余下的问题,疑虑纷然多绪,关注其文学的同道同仁和喜爱其诗其词的万千读者,难免动问:他还能诗词么?偶或为之,能具俘获人心的文学力量吗?此类忖度之于遁入空门之人当是顺理成章的预设猜想。统观弘一法师自出世之日起直至谢世之际的行径作为,似乎有悖于寻常的想象联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们分明看到法师的“有情”宛在。遵循佛家的逻辑,作为地道的皈依弟子,理当断除一切世俗的情感,摒弃所有俗世的“有情”。梳理整饬法师的躬行言说,只是觉得其情更浓更凝,更含文学意味。
1930年5月间法师莅临友生经亨颐、夏丏尊、丰子恺、刘质平等人为其营筑的白马湖“晚晴山房”。5月14日适逢夏丏尊45岁生辰,在寿宴上相与祝酒,倾情诉说,忆及当年种种赏心乐事的良辰美景当下不可复得时,法师感伤不已,潸然泪下,且有二诗偈示之。面对国家纷乱,法师生发出之于国家前途的悲观愁苦:“三界皆苦,国有何赖?”,“声响皆空,国土亦如”,直到法师圆寂西行的前一年,仍书有“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警语以自警警人。这与充满英雄情结,高吟“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亦断头”(《感时》)的李叔同是同“一”而不“异”的。尽管法师踏进佛门以来即小心翼翼、毕恭毕敬地依法行持,亦曾明白不误地宣示文学艺术之类“增长放逸,佛所深诫”,说文学艺术最是情感“放逸”,于佛门持戒不宜,但他还是做了且以一贯之。赴夏丏尊寿辰之前致信夏,说到沿途所历所见的种种“逆恼之境”,称“余虽身心备受诸苦,而道念颇有增进,佛说八苦为八师,洵精确之定论也”。之于文学艺术出身的法师说来,佛门八苦恰便是世俗悲苦的深切映照,无由不动衷情。更有甚者,法师出家六年后,在灵隐寺听其当年的受戒师慧明讲经时,见师父发白齿落、老相兀显,拜谒之际,感怆悲叹,泪落不止。这泪,肯定为其文学的表达积蕴良多。
即或不刻意计较法师的“有情”之泪,仅细读法师入佛时期的诗作,便足以证明经佛理沉潜过滤后的佛思之于诗的蕴育和诗的表达具有何等的助益。法师在佛门行脚11年后,说到自己“十数年未尝作诗。至于白话诗,向不能作。今勉强为之。初作时,稍觉吃力。以后即妙思泉涌,信手挥写,即可成就。其中颇有可观之作”。此中“妙思泉涌”、“信手挥写”等正是诗人创作的最佳状态,自觉“颇有可观之作”,且看法师1931年为弟子刘质平所作七言拗律:
今日方知心是佛,前身安见我非僧。
事业文章俱草草,神仙富贵两茫茫。
凡事须求恰好处,此心常懔自欺时。
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
法师此居方外已近心遂意圆之境,审视、寻味方内情事了无挂碍,之于当年的“事业”“文章”以“草草”自度,有关“神仙”与“富贵”的自我评骘,用“茫茫”结裹。游于佛门已13年的法师仍然追求尘世事体的“恰好处”,时时担忧“此心”的“自欺”。结句直是意韵俱佳的精句,给人启示、慰藉,让读者获得一种恒久的艺术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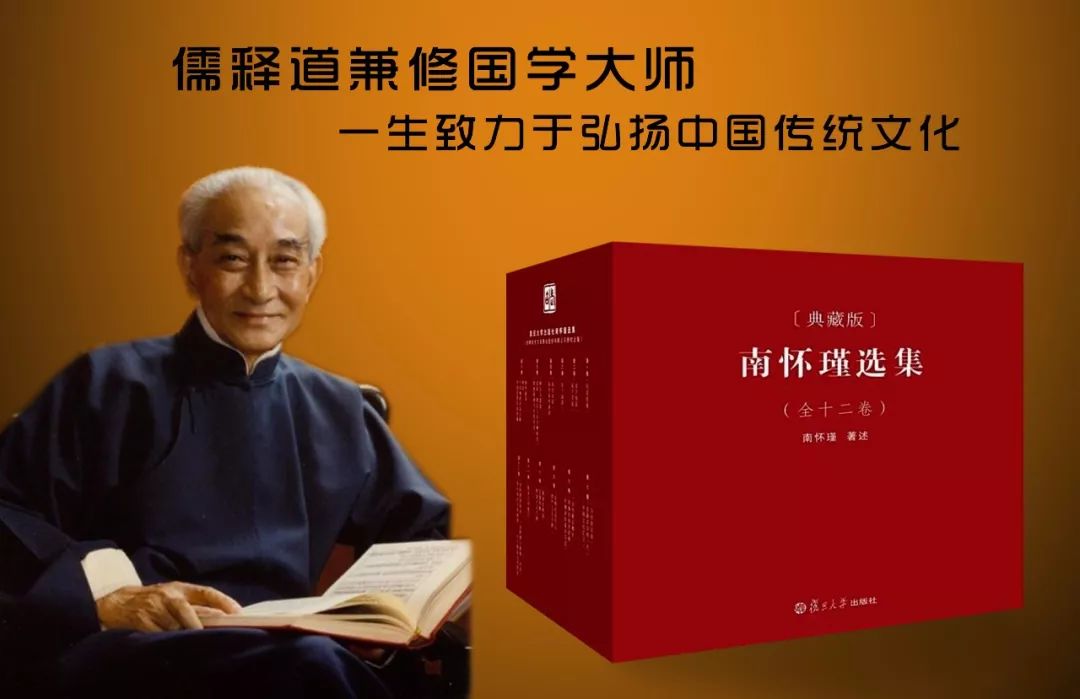
从其方外行持交结考稽,法师的遵从仍然是诗家艺术家的做派、风范乃至意气。法师在24年的佛门生活中基本不收弟子(原先的弟子一二人除外),不仅反复表示不再收弟子,也不出任住持之类的任何僧职。这是佛门的规矩吗?端的是文学艺术的操持!熟稔法师性情、经历的人,大概都知晓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弘一法师出世、谢世的文学品性辨正,遁入佛门的他之于方内外人士,尤其军政官员的见与不见,决非佛的教规使然,一直是诗家意气做主!且看他的对所谓后学的基本教示:“放宽肚皮容物,立定脚跟做人”;“律己宜带秋气,处世须带春风”;“临事须替别人想,论人先将自己想”;“心志要苦,意趣要乐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弘一法师出世、谢世的文学品性辨正,气度要宏,言动要谨”;“经路窄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处减三分让人”;“以恕己之心恕人则全交,以责人之心责己则寡过”等等,此只证实法师的自我修养之高峻,亦可联想法师文学造诣精深。法师自己亦有清醒的认识,“出世”何谓?“出是超过或胜过的意思,能修行佛法,有智慧,通达宇宙人生的真理,心里清净,没有烦恼,体验永恒真理就叫‘出世’。”此状态,亦或称为佛门修持之于文学,只会“心比平时灵敏,颇有文思”。人们有理由相信,出家时已39岁的弘一法师,要想丢弃、灭却原有的“定业”,几乎是不可能的。东方佛家有别于西方基督、天主教门的主要判分,即在佛家自我供认自己有“三不能”,让人读来不只击节叹赏,敢情是心向往之。这似乎印证了文学艺术生产某些规律性的律条,文学艺术家,尤其是卓有成就的大家,一旦成名,往往封闭于社会营造甚或自家制作的神话里,始终找不到新的主题和兴奋,成为艺术创造苦闷的根源。试看极近不惑之年的李叔同,毅然决然地蜕变成弘一法师,如果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考量,其入空门,尽管有“远因”“近因”等种种评估诠解,我们觉得他从自身和文学艺术的逻辑出发,寻找新的题旨和兴奋点是此中重要的原委。
二、“以戒为师”的文学得失
进入空门的弘一法师在佛家“三藏”中,选择了“律”藏作为修行的主导。所谓“三藏”即佛教之经藏、律藏和论藏,其经藏主说定学,律藏讲求戒学,论藏乃叙慧学。弘一法师主修律藏,其个性呈示即其堂皇的“以戒为师”。从法师行持的行迹来看,做功之勤勉、律己之认真、戒持之刻薄、入境之深远,教人感佩不已,甚或常常令方外人伤情泪奔。1921年春暮,弘一法师离杭州绕道上海前往永嘉,对法师心仪已久的刘海粟终于见到了出家三年的弘一:这位曾经风流倜傥、奢华一时的富家公子,如今光脚着一草履,身穿满缀补丁的衲衣,房间卧室只有一张破旧的板床,刘海粟哭了。同年,法师来到白马湖春晖中学,夏丏尊陪饭,看着他认真地把饭一粒一粒划进嘴里,郑重其事地夹起一块萝卜,满含感激地享用着,夏丏尊欲哭。
今天看来法师的自我束制,“以戒为师”的终极所向是“同生极乐莲邦”,以证“无上正觉”。这种苦心孤诣的戒持之于文学的作用是益是损?曰正曰负?应需辨析。
文学的可贵、本真在于情感的人文关怀甚或终极关怀。如果这种关怀一旦具有哲理、佛理的自我约制,那则是对于情感的提纯升华,其文学的品性就有了一种超越尘俗的质量保障。出家近十年的1927年秋,法师云游至沪,住在弟子丰子恺家中亲自主持了丰子恺皈依佛门的拜师仪式,朝夕相处之际,就有了《护生画集》的诞生机缘。种种善缘的促就,俾致“画集”第1册功成面世,子恺先生绘画50幅,弘一法师为画作逐一配诗并亲笔书写。且看《母之羽》一则:画面是四只神情惊疑的小鸡,环绕着一堆残羽,恋母情态叫人锥心不已,诗曰:
雏儿依残羽,殷之恋慈母。
母亡儿不知,犹复相环守。
念此亲爱情,能勿凄心否?
法师还在诗末附注:“《感应类钞》云,眉州鲜于氏,因合药碾一蝙蝠为末。及和剂时,有数小蝙蝠,围聚其上,面目未开,盖识母气而来也。一家为之洒泪。今略将其意作母之羽图。”是册由开明书店出版后,引动强烈的社会反响,广为流传,诸如大中书局、大雄书局、佛学书局等出版机构相继印行,发行量之大在当时出版界颇是罕见。拥赞日隆,歧见亦见。通观这些指陈,反更觉得法师之诗为更具文学意味。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那些非议指责竟然是友朋甚或颇负艺名的艺术家。非议生于世俗,指责未免尘思。与丰子恺有同窗之谊的曹聚仁称《护生画集》该“烧毁”,理由亦极简约明晰:“‘慈光’这一种概念,对敌人是不该留存”的。一向和气容人的丰子恺对此始终未事通融,全方位多侧面迹近不遗余力地申述了自己的艺术主张、艺术遵守。在丰子恺看来佛家的智慧三境是什么意思,曹同学所言,实乃“不知大体”的“皮毛”世俗之论,之于弘一法师“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原则不识未悟。因之,在看到曹无忏悔意后,决然割席绝交。这在一般人看来似乎是一点个人之间的意见歧分,然而对丰子恺说来,事关信念、信仰,翻脸犯颜正好印证了丰子恺持戒向心的定力和对弘一法师敬仰之情的原则回护。

从世俗的角度审视《护生画集》的绘画诗文,似乎画面亦简单,诗文亦浅近,而内中蕴含深情大义、人文乃至终极关怀的慈悲,连艺术家也难免无见甚或不解,对于当时的浮论、舛误,随着时光的延宕而悔初愈深。弘一法师之所以对《护生画集》如此用心用力,期许如此之高,力指何处?高在哪里?直是追求佛境与艺境的完美融合。画集是“艺术品,应以优美柔和之情调,令阅者生起凄凉悲悯之感想,乃可不失艺术之价值。”因而,法师在编选第1集时,身在温州,“精神则贯注于此集之内容与形式。经年揣摩,鱼书往返,对丰居士每页之画稿,必视察其构图之内涵与形式,然后思维恰切之题句。字之大小及所占地位,必求其与画幅相称”,甚至在出版用纸方面,法师都悉心叮嘱,原因全在于让读者一见“即知其为新式之艺术品,非是旧式的劝善书”。有人生发议论:“《爱护动物》,看来合情合理,但却是假仁义。买鸡去宰了吃就可以,倒提了鸡脚,就是虐待动物,倒提与宰吃差距有多大?”这与曹聚仁诟病同,尘俗的生存表相和经佛理透视所见到的生活圣谛相去之遥,不可以道里计。倘或世俗世界为某种有害的观念所笼蔽,即使瞪大眼睛稽考还是不易见真。诸如20世纪30年代的猛克和左联烈士柔石对丰子恺先生的抨击,意见之“左”劣,出语之粗鲁,“令我大吃一惊,很自然地把他的文章与‘文革’中的大字报联到了一起,并感到大字报的‘左’一点也不奇怪了”。《护生画集》为愈来愈多的读者所钟爱,当下益觉其需要与迫切,创作者那“温和慈悲的心肠显现到了极点,一个艺术家的热烈天真的胸怀到了最后最高的境界”。
弘一法师的释门行旅,“以戒为师”,治律治艺,不仅对其文学艺术没有质的减损,反使其趋萃凝菁,正如法师皈依前夜的断食预演所体悟的那样:“心比平时灵敏,颇有文思”。法师在戒持中所表现出来的悲悯慈怜、戒杀护生,确乎到达了极致。1929年,在续写《护生画集》的过程中,一度中止了铸铜字模的书写,人问其故,他在农历四月十二日给夏丏尊的回信中说到:“刀部中残酷凶恶之字甚多,又女部中更不堪言,尸部中更有极秽之字。余殊不愿执笔……”文学爱惜生命,回护朴初,同情卑弱,右袒不幸的根本属性,在法师那里体现得幽微毕现,淋漓尽致。
三、圆寂自证的文学呈示
弘一法师晚年惬意悦心的俗家弟子黄福海始终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瞻仰、深究法师,一次当面请益:“法师在所著《佛法十疑略释》一书中,论佛法非迷信,非宗教,非哲学等,独未说到佛法非艺术,我可不可以这么说:佛门中的生活,就是艺术的生活呢?”法师点头称是。如果从法师15岁时“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的诗句算起,直至谢世前数日遗付友生的诗偈止,法师约略有48年的文学艺术生涯,以1918年前为界,恰恰是方内方外各占24年。
后24年的文学成就似乎渐被文学史家淡忘,人们说到这个时期的弘一法师,首先听到、看到的多半是其修持达到的高度,其“悲欣交集”的释门境界,赢得了海内外、方内外的感佩和敬崇,然而此等境界生发出来的文学效应,却因某种惯常的思维定式被逸出历史的记忆。有知识的认宗教为迷信,没有知识的以迷信为宗教,此种怪异在学界的孑遗,至今不绝。学界乃至喜爱法师为人为文的“弘粉”理该实事求是地研究弘一法师后半生的文学成就,悉心解读法师的文学文本,得出准确的结论佛家的智慧三境是什么意思,给予应有的地位。
与前24年的诗赋歌词相比较,后24年在数量上短了许多,但在诗偈、联语的创作方面却奇峰兀显,且不说《华严集联三百》规模之巨罕有其匹,仅是法师用心之精审,就足以让人感受到诗思的灵光。联语大都“依上句而为次第”,“字音平仄,惟调句末一字,余字不论”,除个别联句,“一联之中,无有复字”。这是何等的文学计较,又是怎样的护法心地!尽管如是,法师仍然“战兢悚惕,一言三复,竭其努力,冀以无大过耳”,这在法师看来,以华严经义集联,到底是“割裂经文”之举措,恐怕“偶一不慎,便成谤法之重咎”。法师寄语后贤,“毋再赓续”,虽含诸多原由,诗学修养的考虑,当是该劝勉的大端。
《华严集联》而外,还创作了大量寺庵楹联、题赠联,其文学意趣、艺术情味,都因了佛家意境思维的照拂,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诸如为晋江草庵所撰书的门联:
1933年冬,法师自泉州开元寺尊胜院来草庵度岁,见寺主苦守出家本务,至心修学悟道,且乐善好施,扶助众生,深获法师衷心,特书是联,以表心旌。联作将“草庵”嵌入上下联句首,一是彰表该寺,二亦深契法意,在佛家看来,草木亦属有情,亦在回护之列,故有“草不除”之说,溥侗亦有名联曰:“不除庭草留生意;爱养盆鱼识化机”,用心传情大致趋同。法师1936年致啸川信中解说此联:“眼前生意满者,生意指草而已。此上联隐含慈悲博爱之意。宋儒周、程、朱诸子文中,常有此类之言,即是观天地生物气象,而兴起仁民爱物之怀也。”“慈悲博爱之意”由文学方式传达出来才能传诸久远。
法师在佛门行脚,随时随地都表现出文学的思忖,始终与文学艺术的知己、畏友、诤友有文学的计较与纠缠:“席间谈到对联,弘公说:南普陀天王殿前当中两根石柱上,有陈石遗老先生写的一副:分派洛迦开法宇;隔江太武拱山门。文有气魄,字也老健可观,不可多得。但大醒法师以为后三字不若易为‘诵浮图’更有画意,可见联语难作。(钱君陶《忆弘一大师》)”体悟到“难作”,法师方时常为诗文的斟酌推敲“自苦”。

法师常籍助佛法观照艺术,认为“最上乘的艺术,在于从学佛中得来”。1936年在厦门期间,对高文显说:“我在街上一户居民的门上,看到这样一幅对联:‘一斗夜来陪汉史,千春朝起展莱衣’,不知是古诗句或是自己撰的,幽香沉着。我在闽南八年,罕见如此佳联。书法也神似苏东坡,当是高士手笔”并嘱其“暇时,可往一阅。能询其撰书者为何人,则至善矣。门内下首边房亦有联……仁者能入门一阅否?”
高文显真的寻到了那户人家,居所主人称对联购于联摊,除夕后,联摊已撤,不晓其人其址。法师闻知,“不胜怅惘”。这自然是文学艺术的追崇,法师精妙的评判和满怀期待的嘱托及其后来的“不胜怅惘”,人们读到的是法师之于文学艺术的精诚相与。
法师居佛期间,对于“世间文字”的思考、传达更趋深刻,日益文学化。1938年农历二月应芗江居士之征,为之题偈曰:
金石无古今,艺事随时新。
如如实相印,法法显其真。
艺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随时新”,根本的命意乃是“随时”随地的“与古为新”。法师将艺术创新、出新之道证之以佛理,愈显精微,法性的理、体,平等不二,故曰“如”,“彼此诸法皆如”,故云“如如”。宇宙在得悟之人看来,“真如”之诸相,实相不二不异,理、实相印,法性传真。法师从佛理的高度,觉察到了文学艺术的质实,文学艺术倘或离“时”脱“新”,何谈其生命、价值?在诗偈中,细心的读者不难读出法师对于“七·七”变局、民族危亡的关注。1941年冬,日本军国主义者进一步扩大了侵华部署,闽南时局更加动荡不宁。时居泉州开元寺的法师,借转道和尚七秩大寿撰联一副,表达了护国护法的气节志向,联语“随时”而“新”:
老圃秋残,犹有黄花标晚节;
澄潭影现,仰观皓月镇中天。
时,法师六十有二,距其圆寂仅余半年多的光景,虽是“老圃秋残”之季,仍恃“黄花晚节”,耿耿赤心,情同碧空皓月,澄潭可鉴,镇守着中天。
近些年有学者将鲁迅和弘一法师进行比较研究,涉及出身、经历、思想、操守、文学成就、文学观。这是一诱人合宜的题目,大面积、全方位地展开该论题,收获是可以期待的。这研究成果中,有人说到,鲁迅见到内山完造家悬有法师书件《金刚般若蜜多经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十分赞赏,于是“从内山君乞得弘一上人一纸”。“乞”字出于鲁迅,可见景仰之深。然而这位文学巨擘如何认识“弘一上人”及其文学成就,未发现有文献记录,但从法师与丰子恺、刘质平、夏丏尊、叶圣陶、钱君陶、朱光潜、郁达夫、马一浮、柳亚子等人的交谊中,读者看到了法师的品行操守和文学造诣。1941年,在此国难当头之际,南社旧友柳亚子在其《弘一大师俗名李息霜,与苏曼殊称为南社两畸人,自披剃大慈山以来,阔别二十余年矣。顷闭关闽海,其弟子李芳远来书,以俗寿周甲纪念索诗,为赋二截》云:“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思。大雄大无畏,救国心无歧。闭关谢世事,我意嫌消极。愿提铁禅杖,打杀卖国贼”。在一般人看来,柳诗对法师似存不敬,从诗境审度,诗意明晓畅达,说两人虽信仰不一,爱国祐民之意同样坚定:“救国心无歧”。因而法师读到此诗,诗心相通,遂奉上《为红菊花说偈》一首,再陈心迹,从中可见法师之于苍生乃至文学的拳拳之心。
文学艺术的成就阻拒着人格品行的种种繁纷诡谲的掩蔽填饰,在终极意义上,反证坐实了文品人品的逻辑关系。法师24年的释门勾留行走,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以戒为师”的诚挚。“惜福,习劳,持戒,自尊”的坚持之于文学艺术的孕育有着怎样的直接关联,这该是一种保障,终有可遇不可复求的光辉时刻。法师文学灵光的届临之于读者、后来者殊难以感动、感谢一言以蔽之。这同时还向世人证明,人格修持的自我完成如何完美地辅佐了文学传达的臻美至善的境界建设。
1942年8月28日,法师自知“近将远行”而写下遗嘱,其中说到:“若见余眼中流泪,此乃‘悲欣交集’所感,非是他故,不可误会”。9月1日书写“悲欣交集”四字交妙莲法师并分别致信夏丏尊、刘质平、丰子恺等人。几封信的抬头因人不同,内容则一,迁化日期空在信中,“为赋二偈,附录于后”。9月4日晚,法师圆寂前瞬间,流下晶莹珠泪,所“附”诗偈曰:
问余何适,廊尔忘言。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这是何等悲壮而伟大的境地!法师“以戒为师”的修持,终得超越尘俗的生死观念,悲慈欣悦交集,悲悯于苍生,欣庆于解脱。而此情此境的诗意传达,则是“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在行将“西往”的法师眼前是春在枝头已十分的生命枝条,仰观天心,所见所觉,不是缺左失右的残月新月,恰是朗照乾坤的满月,无论是人格的修行抑或诗境的进阶,无不法喜充溢而臻于圆满。
由李叔同而弘一法师,不仅是身份操守的淬炼,更是文学艺术的升华。迈入释门的他仍旧“看见花笑,听见鸟语,举杯邀明月,开门迎白云,能把自然当作人看,能化无情为有情,这便是‘物我一体’的境界。更进一步,便是‘万法从心’,‘诸相非相’的佛教真谛了。故艺术的最高境界与宗教相通。……艺术的精神正是宗教的。”丰子恺作为学生、弟子,都是法师方内方外的知音。
法师自将身前身后每一个细节董理安排得如此周详,以吉祥卧姿从容西往,在“悲欣交集”时刻欣证禅悦悲见有情,其涅槃瑞相安详、沉静的生气,给后人信心信力,鼓励鼓舞,这生的力量默如雷霆。那“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境地,定然是佛理证悟时的文学传达,其动人之恒远亦因了文学的品质。
文:王树海 肖菲
供图:王春明
排版:赵明哲李璎月
审核:秦曰龙
随便看看
- 2024-04-18文档介绍:道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文学的联系与渊源
- 2024-04-11惟贤法师:明心见性后,达到妙明真心的境界
- 2024-04-04张松辉:主持的科研课题有“元明清道教与文学”
- 2024-03-29李斌城:文学的灵魂就应该贯穿着唐代思想的几大渊薮
- 2024-03-05成卓华摘要: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知识
- 2024-03-02圣严法师:佛教修行不应该有什么善恶之分
- 2024-03-01韩愈:哪位文学家是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人?
- 2024-02-28厦门石峰岩寺主持净雄法师接受中国网专访
- 2024-02-14潜藏着日本人怎样的生死观?:法师吉田兼好对生死的探索
- 2024-02-12净空法师:人生怎么活,自己找心宽
- 2024-02-07净空法师:佛法是究竟之法:道出一切苦的根源
- 2024-01-27(知识点)中国现代学术的开端——《自话文学史》
- 2024-01-22印顺法师应邀出席第六届中国生态文明论坛年会
- 2024-01-20基于佛理考察中国佛教文学思想史上的独特价值
- 2024-01-17:文学论文,儒家,和谐取向,社会哲学
- 2024-01-17“生态文学”是一种现代思想观念在文学领域的表现
- 2024-01-14净慧法师:佛的威力有多大?怎么入涅槃?
- 2024-01-13(李向东)道家的主要思想主张与深厚的知识背景
- 2024-01-12邓乐:年第27卷南昌教育学院学报文学艺术
- 2024-01-11(知识点)中国古代文学常识大全,值得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