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佛法亦宗教亦哲学言思立意之高
汤用彤:佛法亦宗教亦哲学言思立意之高
陈 源 源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中心硕士生)
“佛法亦宗教亦哲学。宗教情绪,深存人心,往往以莫须有之史实为象征,发挥神妙之作用。故如仅凭陈迹之搜讨,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哲学精微佛家生死观的哲学思考,悟入实相。古哲慧发天真,慎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深弘。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寻求,而乏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其糟粕而已。”汤用彤先生言思立意之高,为后世学者垂下谨慎笔墨之范。
让我想起此话的是手边方广锠先生这本讨论印度初期佛教的新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薄薄一册,作者试图回答的是些源流问题——老问题,日久积弊,会模糊隐蔽得不像问题,或者给人感觉已得解决。
本书分八章:1.古印度的两种文化传统 2.初期佛教的年代、分期及其它 3.初期佛教的起源 4.初期佛教的思想 5.初期佛教的五阴与无我 6.初期佛教的灵魂观及其对后代的影响 7.初期佛教的禅定修持 8.佛教的时间、空间与世界模式。 前三章讲佛教产生所依托的文化土壤和时代背景,中三章谈初期佛教基本思想和几个关键概念,末二章单论专题。结构明晰,层层剥离,文献考古与宗教哲学双轨并进,相互发明。
这里只略说几个笔者关注点佛家生死观的哲学思考,以期抛砖引玉。所谓关注点,即读此书时,素来的模糊印像凸显成问题再茅塞顿开处。
一.沙门思潮。
人们对沙门思潮的一般看法是,恒河中下游婆罗门教失去人心,日趋衰落,因而在反婆罗门、反婆罗门教的沙门思潮中,佛教兴起[1];有时还照印度正统派哲学的排序,把佛教置于奥义书之后。但据《摩奴法论》中“婆罗门中国”的区域范围和学术界对奥义书的断代,公元前500年左右,约释迦牟尼创教时代,(雅利安人进入西北印,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而成的)婆罗门教势力还局限于恒河上游地区,大约刚开始进入恒河中下游;这股外来新力量给当地土著社会结构和文化冲击很大,相应地受到土著文化的抵制,而沙门文化是当地土著文化的代表。佛教正是产生在婆罗门与沙门两种文化激荡交汇之中,并且从反对婆罗门教“祭祀万能”、主张“梵我一如”的奥义书思潮中吸取力量。对佛教产生时代背景的误会,实质上是没有搞清雅利安文化与印度土著文化的关系、雅利安文化和西北印度土著文化孕育成的婆罗门教文化与恒河中下游土著文化的关系问题。[2]
二.迦毗罗卫城。
佛陀的故乡迦毗罗卫城,在我国学术文章乃至权威工具书中,解释为蓝毗尼西面约23公里处的提罗拉科特,这是基于1895年英属考古局和1899年印度考古学家考古成果而得的结论;但七十年代初印度考古局在蓝毗尼西南15公里处庇浦拉瓦又有新发现,并且能够解释法显《佛国记》与玄奘《大唐西域记》之间龃龉处。我国彼时的内部状况,导致讹传至今。
三.古印度的两个传统:禅定与苦行。
禅定瑜伽出现在印度河文明印章中却不见于《梨俱吠陀》,可见与雅利安文化无关。典型的瑜伽行者印章中,瑜伽者头上角的形象应是树枝—— 树下清凉好修持,树神崇拜很广泛。土著文化中的此种因素也是佛教的天然养分,释迦牟尼从降生到涅槃一生中的重要阶段都与树相关,过去七佛、弥勒佛也都在树下成佛,阿弥托佛净土有道场树……树总是被特别提到。雅利安文化与土著文化相融合,吸收了瑜伽这种方式,但初期奥义书虽已提到“禅观”却未给出“瑜伽”这个名称,直到中期奥义书时期“瑜伽”才正式出现,后来修持逐渐系统化,融入婆罗门教“梵我一如”理论体系。同样地,早期佛教文献中也看不到“瑜伽”这个词,有的只是“禅观”。这便从另一角度说明佛教的瑜伽修持理论同其它理论一样,与婆罗门教的奥义书思想平行发展,相互影响,不存在前后继承关系,它们的共同源头,都是古印度的土著文化。
初期佛教禅定主要是四念处、数息观、慈悲观和因缘观,禅观不是目的,而是照见无常、了脱生死的宗教践行手段。神通与禅定关系微妙,古印度人普遍相信正确修持瑜伽可得神通,一般群众都很敬畏和崇奉,但早在史诗形成时代[3]神通即被正统教法嗤为偶得之细末、证得梵我一如的障碍,而正是群众的崇奉膜拜导致瑜伽技艺的退化[4];神通可作为修习层次甚至觉悟的验证,但佛陀也严禁弟子炫耀和迷恋神通。以西方实证科学的眼光审度,类似的“东方神秘主义”本身就像是宗教;科学也好、神通也罢,人类依自身认知能力给出的有效性解释,来不断界定“神”与“通”的疆域消长进退。
苦行也是印度土著文化的重要传统,也不见于《梨俱吠陀》,到了婆罗门教时期却很流行。苦行,梵文为Tapas,意为热、火,可理解成通过苦行可得到神秘的“热”。古印度人认为苦行得热射光,即获旺盛生殖能力;求子繁衍是其原初动机,而它种苦行法力和神奇表现,实为晚出[5]。苦行者通过肢体运动或折磨而得到某种心理感受或神秘体验,婆罗门教将其抽象出来汤用彤:佛法亦宗教亦哲学言思立意之高,认为其独立于世界,甚至能够创造、支配世界。
释迦牟尼生活的时代,恒河中下游苦行修炼盛行,他本人也有六年苦修经历,无所得终放弃。但传统往往坚固得很,佛教戒律生活中的“四依住”长期存在,后来虽被佛陀放弃,但仍被佛教徒认定是上根机之人修行捷径;提婆达多与佛陀间的矛盾,其根本也在于对苦行“本色”的保留或扬弃[6]。这个问题,再进一步说就是,初期佛教有别于其同时代大背景文化的特出性在哪里,或者,究竟怎样定义初期佛教[7]。
这里闲话一句,或许会引出更现实的启发。笔者留学印度期间,寓所中的印度邻居即来自比哈尔佛陀故乡一带,二十八岁,大学化学教师,自幼修禅定,习同饮食睡眠。大学毕业五年来他编写了十八本大部头教材,每天除五六小时睡眠外几乎都在高度专注地工作。这样一种健康饱满的身心状态和工作效率,在我国青年中,无论僧俗是不多见的。
四.轮回与涅槃
印度所有的宗教理论与修持都是围绕解脱轮回、永恒涅槃这个主题而展开。有文字可查的轮回思想最早可见于《百道梵书》;《梨俱吠陀》一派明朗乐观风貌,没有轮回观念。轮回观念最初大约出自古印度人对周而复始自然现象的观察并反用自身,并不含有伦理意味。作者大胆推测:虽然文献上印度河文明文字尚未释读,但轮回观念很可能在印度河文明时期即已产生。
佛教涅槃分有余依涅槃和无余依涅槃汤用彤:佛法亦宗教亦哲学言思立意之高,如果联系大体同时期的耆那教“七谛”和奥义书的“四位说”[8],其解脱路径虽异,精神却一致。
涅槃到底是什么?作者澄清西方学者对“火之消散”这个譬喻的僵化诠释和断见曲解[9],及其对我国研究者的影响。涅槃境界究竟如何是超言绝象的,只能靠行者在调控身心、探索神志过程中亲证;印度的佛教徒把它抽象出来,与人类终极关怀、与哲学本原相结合,以毕生精力为代价,以“四向四果”为进阶,朝向清净妙乐、圆满无缚之境。
五.我(阿特曼)与无我
“我”,梵文Atman阿特曼的意译,原意为气息。奥义书将它引申为个体灵魂,含义复杂,各派解释不同。奥义书哲学最高峰,是提出第五种阿特曼即妙乐阿特曼,总摄前四种阿特曼佛家生死观的哲学思考,构成五藏说—— 五种阿特曼层层包覆,核心部位是妙乐所成阿特曼,真、知、乐三位一体,在本质上与世界本源梵一致;妙乐阿特曼受物质染污由梵下降,渐次展开而成其它四种阿特曼,轮回三界,如果摆脱物欲缠缚,净化染污,即可升大觉位,回归如如不动“梵我一如”境地。
佛教与奥义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长阿含》称佛陀“本由寂灭来”,“还到本生处”,“究竟入寂灭”,修行就是要“诸弟子尽受教训,梵行具足,至安隐处”,“逮得己(阿特曼)利”。初期佛教不仅不否认我(阿特曼),而是对阿特曼加以积极保护、净化,以达涅槃。“无我”,在初期佛教,准确地说是“非我”,强调不能受五阴阴覆、以非阿特曼的东西为阿特曼而沉溺,不能执有为法的非我为无为法的我而成痛苦轮回根源;从析空观的角度说五蕴无我,是后来部派佛教时期的观点(p. 170,梵文 前后期译经中的涵义变化)。
佛教中的我(阿特曼)与奥义书的妙乐阿特曼不同处在于:佛教反对世界本源梵天创世和梵我一如,反对赋予阿特曼本体论意义和有为造作特性;反对妙乐阿特曼可展成四种阿特曼并兼备此岸、彼岸双重特性,而认为阿特曼无染无为;阿特曼是超言绝象的绝对主体,但奥义书总是设法描绘其精妙,而佛教则采取“无记”,即严格的不叙述主义(无法描述,出口即落言筌,必须靠宗教修行亲证,而不是通常人们所理解的逃避不回答)。
六.灵魂
初期佛教把绵延的意识之流抽象成一个独立于肉体的超自然存在,既然它同样承担起人们赋予灵魂的那些功能,就应当承认它也是灵魂的表现形式之一,而不是以有无迁流为判断某一形神体系有无灵魂的尺度。此处,作者以《那先比丘经》为依据,认为该经虽是部派佛教时期成书,但其中关于灵魂的讨论非常丰富,既有初期思想又有部派内容,正是考察“识”向“业”过渡、灵魂观发展的重要资料。
《那先比丘经》在生前、轮回、涅槃三个阶位上都有某种超自然的存在;尤其在第一、第三阶位上[10],如果不否认奥义书中的“认识所成我”和“妙乐阿特曼”是灵魂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也不能否认初期佛教中的灵魂形式。这种灵魂观中,不能自圆其说的轮回主体问题、因缘生成联结无常迁流与永恒存在问题,后来的有部试图用“中有”、“退”与“不退”来解决。佛教理论的这两个内在矛盾,根本决定了其后在轮回、业和“自我”问题上的发展方向。
作者多次强调,初期佛教就总体而言是宗教实践,不是哲学体系,释迦牟尼是伟大的行者,不是坐而论道的哲学家;但既要传道,自然要讲道理,其中粗糙的思辨成份正是哲学因素。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今天眼中的矛盾,正是初期佛教的圆融所在。
全书行文一如既往,朴厚晓畅,不掉书袋,少名相缠绕,不排斥新读者。引用佛经记载,多以自己语言概括而出;需在精微处讨论计较处,方引大段原文。
白璧微瑕。第一章中前两节谈印度风土文化与印度河文明时(pp.1-13)、第三章谈雅利安文化进入西北印时(pp.91-93),如能配以若干幅相应时期地图,空间变迁可一目了然;重视地图是中国史地研究中的优良传统,生动运用,事半功倍。转述或评论国外学者观点时,如能详附参考文献,将便于读者查阅(如p.150)。
作者展望信息时代提供的广阔对话平台,今人借以越过纷纭杂说直溯本源。如果各国学者在文献资料和分析方法上的沟通能更开放[11],则地域、语言、民族、部派、教法等如何绕穿于时间纵轴将佛说带到今天,厘清虽繁难,却并非不可能。[12]
作者在序跋中交代,原初构想的研究课题与方法未能在本书中全部落实。再看学生时代即属意的印度佛教研究,二十余年后方才落墨,有时代的迁流,有个人的安住。书中几处,问题提出,点到为止,留待他日云云(如p.109,佛教如何吸取释迦族、恒河中下游土著文化,又如何突破其局限;p.185,详细对比奥义书、顺世论、数论、耆那教与佛教自我观的异同)。作者审慎略笔处,正激发细心读者独立探求的兴趣——进入另一种文明的情感与思想,尤其又是古代甚至史前[13],对其基本语境的理解、记忆与想像[14],要靠个人认知机能和探测工具的全面开发了。
圣雄甘地说,印度文化只有三种要素,耕田的犁、手工纺织机、印度哲学。酷热燥闷、王国兴替、禁欲忍耐……极致生存状态下的极致生命体验[15],不断输出南亚次大陆而与他种文明共享。这种生命体验被叫做宗教、哲学、或文化,不择肤色国界,甘露遍洒,润物无声。可这片土地被如何认识的呢?“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林伽崇拜的宗教,又是扎个特纳的宗教;既是和尚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16]文明之外的旁观者容易看到的是矛盾表面,不明就里,无法整合,反而倍感难以理喻之苦恼。这片土地又得到了何种回报呢?谁能直面并安抚奈保尔的“幽暗国度”、“受伤的文明”、“百万叛变的今天”[17]?
[1]如,龙达瑞《大梵与自我:商羯罗研究》,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2] , Early India: From the to AD 1300, Books India, 2003, pp.98-173.
[3]有关史诗创作年代,参见刘安武《印度两大史诗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pp.19-31。
[4] , The of and Yoga, The of , Vol. 45, Issue 1 (1924), pp.1-46.
[5]赵国华《热与光:苦行与精进》,载《南亚研究》,1991年第四期。北京大学哲学系&山东大学哲学系编:《东方文化集刊2》,商务印书馆,1997,pp.51-66。
[6] K.T.S. Sarao, and of , R&R , Delhi, 2nd , 1999, pp. 107-1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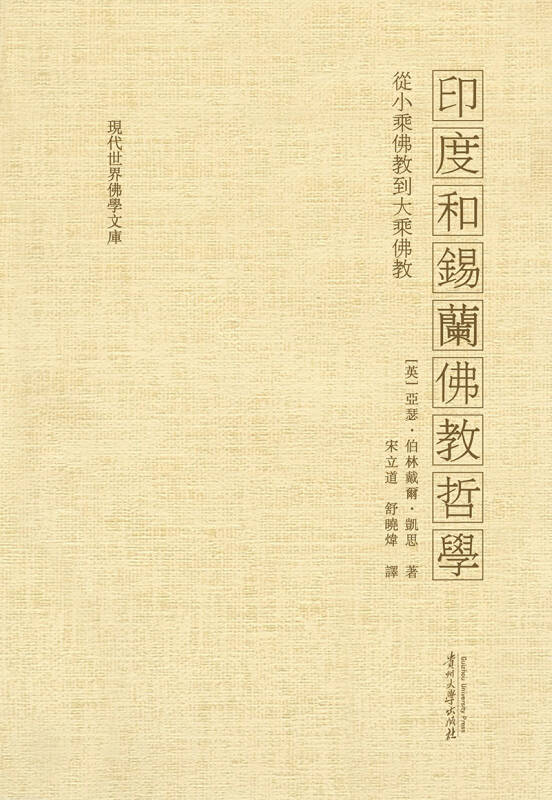
[7] , The Two of in India, Delhi: , 2000.
[8]S. & C. A. Moore, A Book in , Press, 1957.
[9] F. , How began, Press, 1996, pp.1-26, pp.65-95.
[10]吕澂《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11]杨梅《第十三届国际佛学大会综述》, 载《华林》第三卷,中华书局,2004,425-440页。
[12]这里援引一段我国佛教、佛学届以外的广义文化学者对此问题的认识。我国英语语言文学界前辈王佐良先生在1984年写道(王佐良《翻译:思考与试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19页):“……一个有心的译者往往感受也特别深切,尤其在两种文化第一次大规模接触的时候。中国历史上有过几次大规模的佛经翻译,但是我们所知无多,而想提的问题不少,例如:高僧们在翻译过程中有些什么体会传了下来?为什么他们有时意译,有时则把词句连音照搬过来,甚至整本经都这样?有些什么经验教训?此外,我们难道不能透过译本去看看当时中国文化的情况—— 语言的情况,宗教的情况,人们学习外语的情况,士大夫的思想情况,一般人的心理情况,等等?那样一深入,一扩大,我们的翻译史也会写得更活也更富于启发了。”王先生所处时代的学习、科研维度没能给他开解疑惑的基本空间和材料,而他的独立思考却完全触到了问题的本质。1987年,王先生有了行动构想(同前,5页):“断代翻译史—— 现在似乎……可以集中研究一个重要的翻译时期了,如唐朝译佛经最盛时。这类研究要多找一些资料,要有较长的成片成段的例证,要突出若干重要译者,替他们摄特写镜头;要从社会背景和文化交流着眼;有历史家、思想家、佛学家的合作;总之要比已有的叙述做得更丰满更深刻。”王先生二十年前期盼的学术力量整合,所幸今日已有迹可寻;他给出的那些问题被碰到的却仍只是很小一部分(金克木《梵佛探》,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412-422页;金克木《印度文化余论——<梵竺庐集补编>》,学苑出版社,2002,9-22页),欲完满解答,尚需时日。(王佐良先生(1916-1995)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牛津大学研究院,任教于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先生融会中英两种语言技艺与文化修养,文字敦良清峻,重见地与风格;其作品量少质醇,篇篇隽永,我国英语学习者几乎无人不晓。)
[13] , of India ( ⅩⅩⅥ), Press, 1989. Daya , : A , , 1991.
[14]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15] Smith, Why , San , 2001.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6-1985,114页。
[17]V.S. 奈保尔《印度三部曲》,北京三联书店,2003。
随便看看
- 2024-04-29南怀瑾老师:佛教是宗教,亦是哲学?什么是真?
- 2024-04-29范明静:佛教精神的独特的“心物观”
- 2024-04-2720152015江苏高考满分作文:智慧三境佛家有智慧
- 2024-04-27:智慧还能分为三境:山,海,天
- 2024-04-27(每天1分钟读1本书)“轴心时代”的著作:《薄伽梵歌》
- 2024-04-25理学如何体现吸收道家和佛家思想 脊椎矫正﹚,六个月开始移筋换骨﹙
- 2024-04-25汲取二程理学精华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领读人)
- 2024-04-23佛教传入的确切年代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 2024-04-22(李向东)世界上最经典的十句话(建议收藏)
- 2024-04-22南怀瑾老师:顿悟开悟智慧,让人醍醐灌顶,当头棒喝
- 2024-04-22风水堂:矮个子小沙弥的故事
- 2024-04-21佛家智慧三境 江苏高考满分作文:山,海,天。天!
- 2024-04-21(深度好文)用毅力安排人生时间的时间!
- 2024-04-20优秀52句,多看几遍一定会有大提升!
- 2024-04-20佛家生死观的哲学思考 2005年6月17日讲于北京大学)提纲一
- 2024-04-20(连载)法句譬喻经(二十五)中的一个故事
- 2024-04-16道家思想传统武术文化道论气论天人合一论论文
- 2024-04-15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概括起来了!
- 2024-04-15近读王振复新著《南北朝佛教美学史》
- 2024-04-14中国人的诸子生死观:生死到底有着哪些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