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
:“仁”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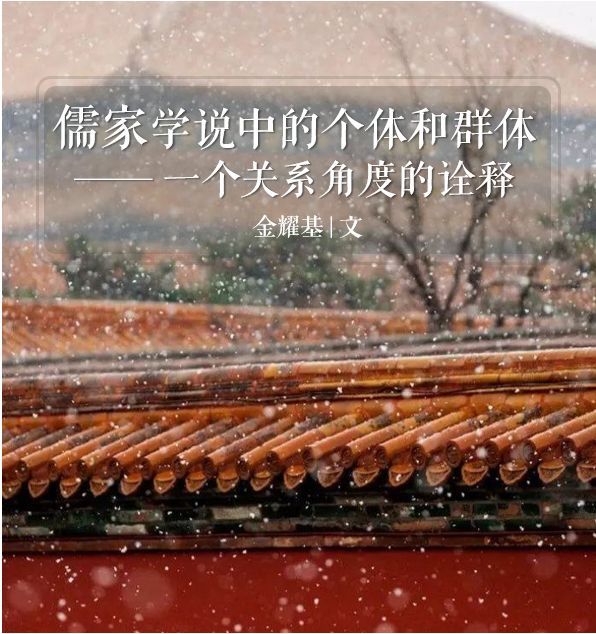
孔子在一个以人为中心的世界里发展了一套人文主义的伦理学。对于孔门弟子来说,其基本关怀始终指向现世的社会生活。如何建立一个世俗的和谐秩序,这是儒者必须面对的一个基本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他们十分重视个体和社会的有机联系,认为两者是相互依存,须臾不可或离的。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问题在于,“社会”的定义经常都是含混不清的,一如人们在谈及大于家庭的单位时,往往并不给群体的概念以一个明晰的界说。
“仁”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在儒家伦理中,“仁”必须通过个体自我的自觉努力方能达致。这意味着,孔子将个体视为一个能够达到道德自律,成就圣人境界的积极主动的自我。作为儒家伦理之基石的“恕”归根到底只能由个体自我去践履和完成。在孔子看来,“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事实上,“恕”(亦即推己及人的能力)乃是儒家伦理的关键概念。就此而言,儒家伦理的一个突出特征即是所谓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唯意志论”,此点容后再作讨论。这样,儒家之特别关注自我修养的问题,便不足惊讶了。的确儒家学说思想核心在于而道家思想核心在于,儒者都毫不含糊地肯定自我的道德自律,若欲成为君子,一个人就必须抗住各种外部的和内部的压力。
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个体和群体的关系问题。首先,儒家从来不将个体视为孤立的存在,恰恰相反,人被界定为社会底存在。诚如胡适所言:“儒家的人生哲学认定个人不能单独存在,一切行为都是人与人交互关系的行为”。毫无疑间,孔子的根本目标就是“成为人中之人”。个体一旦离开人群,就无以成就任何事业,如果不把仁置于社会世界的框架内,它就什么也不是。事实上, “仁只能在人际关系中,亦即在社会世界的框架内加以培植和发展。”。从儒家的观点来看,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就是“五伦”,这五项关系分别为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妻之别、长幼之序和朋友之信。五伦被视为中国社会秩序的基本规范。杨庆堃指出:
五伦以亲族关系为轴心,构成了社会和道德训练的基本内核。个体几乎从意识到其社会存在之日起,就开始接受这些基本规范,最后他完全受制于这些规范,甚至连其评价满足与挫折的标准也是由此出发而建立起来的。
用贝拉(R.N. )的话来说,五伦构成了儒家社会的“中心价值系统”。
在五伦中,属于亲族关系的居其三,其余两项虽不是家庭关系,却是以家庭为参照构架而展衍出来的。君臣关系按父(君父)子(子民)关系构成,而朋友关系则按兄(吾兄)弟(吾弟)关系构成。诚然,真正的基本亲族关系仅仅限于主要的家庭关系,但是还存在着其他许多种次要的家庭关系。在最早的汉语辞书《尔雅》里,用以标示各种家庭关系的专门辞语逾百。 许多非家庭的社会关系以结构和价值方面来看也同样是以家庭系统为模板而构成的,例如师徒关系仿效父子关系而运作,从而形成一种准亲族性的纽带。因此,中国的家庭系统本身就有被视为“中国的社会系统”了。用帕森斯的话来说,中圆是一个“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其间家庭以及从中派生出的家族系统在整个社会中占有非同寻常的战略地位。
在儒家的家庭系统中,父子关系至为重要,孝的原则居于个人、家庭和社会存在的中心位置。诚然,儒家学说中还蕴含着其他一些文化理想,然而,“孝的原则是传统中国之主要身份( )的源泉,它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想,而自我形象的其他一切形式都要依此标准来进行评判。”值得一提的是,在儒家的价值系统中,每一个别的角色并不是被置于一个绝对等级序列中的。五伦中的五对关系最初是对称的(亦即平等的),但在影响深远的《孝经》一书中,孝的概念被推到了中国伦理系统的中央位置上。个体的独立存在得不到承认,个体于是淹没在以家庭为本位的伦理系统之中。在这样的文化设计下,父子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就不再是对称的了。不唯如此,中国的法律制度还为这种不对称的权威关系——它已经成了儒家家庭伦理的一种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形式——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持,瞿同祖列举的大量材料表明,中国的法律经历了一个“儒学化” 的过程,而正是通过此一过程,家庭的等级和谐秩序才得以作为一种毋庸置疑的价值而确立下来。有学者指出:
在传统上,中国人很少将自己视为一个孤立的个体儒家学说思想核心在于而道家思想核心在于,他是其父之子,其子之父、其兄之弟,换言之,他是其家庭的一个有机成员,是一个具体的个体,在家庭的血缘氛围里活动、生活,并获得其存在……。每个家庭均有一家之主,他的妻子、儿女、媳妇、孙子及仆人都必须对他绝对地服从。在我看来,中国的法律系统在推行孝道方面可谓尽精微,举世无匹。
诚然,在中国的家庭里并非完全看不到个体的踪影。如果将中国与日本家庭中个体的角色作一比较,就能十分清楚地见出这一点。在日本的家庭中,个体作为一个单位完全被家庭所淹没。但是,在中国的家庭里,由于强调等级分明的和谐秩序,因此就必然使个体遭到种种结构性的强制。阿波特( )指出:
个人主义存在着,但却被内在化了,不能通过社会的行为表达出来……自我修养不同于自我实现,因为前者是有序的,而后者则是自发的。
在家庭里,个体不愿坚持自己的权利,唯恐有破坏和谐之嫌。威尔逊( )认为,中国社会系统的显著特征在于,它格外地强调群体的忠诚,并且不遗余力地坚持捍卫「忠行」的理想(例如为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在论及个体在家庭里的地位时,杨庆堃作出了如下的分析:
西方的个人主义概念同传统中国家庭的精神直接相悖,它与家庭的传统式忠诚也是格格不入的。自我修养是儒家伦理的基本主题,一个小孩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按照传统的方式接受这方面的熏习。自我修养并不是要通过确定、限制和保障个人的权利和利益或通过个人之间的权力、利益的平衡来解决社会冲突,它毋宁要求个人为维护群体的利益而作出刍我牺牲,由此为社会冲突提供一个解决办法。
杨庆堃的分析表明,在儒家关于人的概念中,个体的自主性的确是受到强调的,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个体必须生活在,并且从结构上置于家庭之中,家庭,而非个体,是传统中国的基本社会事实。家庭,而非个体,不断地当作一个等级性的整体来加以强调的。由此,梁漱溟所说的“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便不难理解了。张东荪也把也把中国文化中的个人视为一个“依存者”。
康有为把传统家庭的“废除”视为现代公共责任得以实施的前提条件,谭嗣同猛烈地抨击“纲常”伦理,毫不妥协地呼吁要“冲决网罗”;突破儒家的社会纽带。的确,康、谭之持有此种见识不是偶然的。在五四期间,“孝”的原则遭到了文化上全面的抨击,其结果是,至少在知识界,人们对诸如服从和权威之类的儒家家庭规范提出了质疑与批判。

群体的弹性
中国人所秉持的强烈的群体取向被绝大多数的(如果不是所有的话)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社会学家视为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按照涂尔干派的社会学家的看法,群体具有外在于个体的自主生命。作为一种主导性的社会单位;中国的家庭确拥有一种将个体置于依附地位的结构力量,这一社会学事实不容否认。但是,另一方面,亦必须指出,社会结构在塑造个体行为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从结构的观点出发去看待人类之社会行为虽然并无不当,但却并不充分。布鲁默(H.)从符号互动的立场出发认为:社会组织提供了一个框架,各个行动单位均可在其间发展其行动。诸如“文化”、“社会系统”、“社会分层”或“社会角色”之类的结构特征为他们的行动设置了条件,但却并不决定他们的行动。
如果仅仅对中国人的行为(尤其是中国人的家庭行为)进行结构分析,那就容易使人对中国社会得出一种“过份儒学化”观点(over- view)。 “过份儒学化”观点是说,个体的行为被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解释成了儒家规范和价值之彻底内化的结果。有关中国社会之结构观念的根本弱点即在于,它没有认识到组成社会的个体都拥有其“自我” ,而如前所述,儒家伦理所特别强调的正是此种自我。
儒家“正名”的概念要求名实相符,旨在通过建立一个明确的角色系统实现社会的和谐。在儒家“礼”的社会关系中:“仁”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每个人都被指派了一个适当的位置,因此,大量的行为均可按照角色予以解释。但是,正如朗格( Wrong)正确地指出的,一个人并不只是一个角色扮演者,如果仅仅对儒家的价值规范进行结构分析,那就无法充分地理解中国人的行为。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彻底的儒学化乃是不可能的,且也因为在儒家伦理的内部有着一些前后矛盾的价值和规范。的确,在儒家的文化取向与结构规范之间存在着不少紧张和冲突,所谓忠孝不能两全,公私不能兼顾,以及仁礼之间的基本冲突都说明了这一点,其中尤以个体自主的价值与家庭主义之服从的规范两者之间的冲突最为突出。“有许多人由于其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因而就没有机会按照他们一直被教导要加以崇奉的价值去行事。当文化价值被这样一些人所内化时”,便会出现上述的紧张和冲突。这些现象,用默顿()和巴伯()的话来说,都是“社会的两向性”( )的典型实例。 “社会学的两向性”这一概念对于理解社会角色结构的动态性质有着极大的帮助,它使我们更易理解那些行为是不能简单地归于固定的儒家角色和规范的。特纳(Ralph )提出的“角色抉择”(role-)的概念也为静态的、决定论色彩过于浓重的角色概念提供了一个矫治之方。他认为角色关系“充分互动的”,而不仅仅是规范的或文化的决定论的延伸;实际的角色关系或多或少产生于理想的规范与灵活的角色抉择过程——他人对他的结构性要求与自身的目标和情感的需要——之间的一种稳定的动态调和。特纳在角色问题上所持的动态观点对于分析儒家的角色行为具有重要的启发生,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儒学赋予个体自我以大量的自性。儒家的“己”作为一个动态实体,能够改变和创造同他人的角色关系。当我们开始考察中国人的群己关系时,承认自我的自发性格的本质以及角色结构的动态性格是极为重要的。
儒家把人类共同体分成三个范畴:己、家和群。对于儒家来说,重点主要落在家上,由于这个缘故,儒家伦理在家庭的层次上发展了一个精细的角色系统。相对地说,儒家于群的概念表述得最不清楚。应当指出,从概念上说,家也是一个群体,为了在分析的层次上对两者作出区分,“家”可以称为“家庭群体” ,而“群”则指“家庭以外的群体” ,或简称“群体”。儒家理论从未正式讨论过“群”的概念,“群”始终都是一个游移不定的概念。费孝通正确也指出,群己界线是相对而含糊的,在中国传统中从不存在群己界线这回事,“群”的外部界线即是“天下”这一模糊不清的概念。英国人类学者华德( Ward)也指出,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特征就是相对地缺乏一条明确的界线来规定“内群体”。就连“家”这一表征基本的社会单位的辞语在概念上也是极不清楚的,有时它仅仅包含核心家庭的成员,但有时它又包含同一世系或氏族的全体成员。不仅如此,“自家人”这一习用语可指一个人所欲包含的任何人,“自家人”这一概念可依具体情况缩小或扩大,理论上,它可以延伸到一切人,乃至变成所谓的“天下一家”。群体没有明确的边界,在我看来,这一事实对于研究集体主义(或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家庭群体的模糊性或灵活性给予个体以广阔的空间去建构其自身的家族关系网络,因此,家庭和其他群体的边界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己”的决定。
据史华慈( I. )的意见,在儒家的社会伦理中存在着一系列的对偶现象(),其中之一就是修身(修己)与治国平天下之间的对偶。史华慈对儒学的问题处境()的思考为儒家社会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仁”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这方面的问题还得进一步探讨。在我看来,儒家的社会伦理能在个体与群体(家庭以外的群体)之间建立起一个“可行的联系”( )。儒家社会理论的问题的根源即在于,群己界线未能在概念的层次上明确地表述出来。
如前所述,儒家十分重视经过调节而达成的均衡与社会和谐。但是,如果我们更加细致地考虑此一问题,就会清楚地看到,儒家的社会秩序乃是建基于“伦”的概念之上的。“伦”可以解释为一组制约着社会关系的规则,它主要关注的是“别”——亦即角色关系的等差——的问题。费孝通把“伦”视为“差序”,认为它指示着一个分有等差的身份秩序。“不失其伦”的意思是说,每一角色关系在秩序中均有适当的位置,所有的角色关系都按照有关个体同“己”的关系的亲疏远近程度而有等差。“伦”囊括了广泛的社会关系,其中“己”占据着中心的位置。换言之,人伦是一个人角色关系网的总和,而五伦则构成一个人的主要角色关系的基本原则。在此必须强调,尽管儒家的社会理论告诉我们个体应如何通过适当的“伦”而同其他的特定角色发生关系,但是个体同群体应有怎样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却未得到细致的考察。换句话说,个体的行为被认为是以“伦”为取向的。以“伦”为取向的角色关系在本质上则是个人的、具体的的和特殊取向。在此,要对个体舆群体关系的性质进行简单的概括是十分困难的。如前所述,由于群体的界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体决定的,个体乃是角色关系网的建构者,因此所有的群体价值和利益也就都无不以“己”为轴心。费孝通把这现象称为“自我主义”。在他看来,自我主义并非“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杨朱学派的独专之物,事实上儒家也赞同此一概念。费孝通充分地认识到杨朱学派与儒学的区别所在,按照他的看法,前者完全忽略了自我主义相对性和灵活性,因而就仅仅专注于自我,而后者则充分认识到自我主义的相对性,并能按情况的需要由自我推及家庭和国家。从而,虽然儒学流派杂多,但无不强调“克己”的概念,这是绝非偶然的。“克已复礼”被认为是达到仁的。这一伦理原则显然是要让个体对自己与他人的道德相关性给予特别的关注。重要的是,尽管儒学承认群体的概念,但是个体往往只能确认他同群体中的某些特殊个体而不同群体本身的道德关系。“伦”只是在同个体而不是同群相关联时才存在。当认识到这一特殊的事实后,我们就不简单地把西方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概念机械用于分析中国的现象。

个体的关系取向
许多学者都对中国社会系统的内在逻辑作出了解释,其中梁漱溟是用力最多,见解透辟的一个。在对中国的社会系统和其他的社会系统作了一番苦心的比较之后,梁漱溟得出结论说,中国社会既非个人本位,亦非社会本位,而是关系本位,在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系统中,强调的重心主要落在特殊个体之间的关系上。他说不把重点固定放在任何一方,而从乎其关系,彼此相交;其重点实在放在关系上了。
换言之,在儒家社会理论中,我们可以说,人被安置在一个关系网络中——人乃是“关系的存在”( being)。社会学者潘光旦也令人信服地论证说,中国的人文价值系统极其重视“旁人”,他认为,儒家思想深切地关注一个基本原则,此一原则包括两个主要的问题:个体之间差别的种类和个体之间关系的种类,他说,这两个问题加在一起就构成了“伦”的原则。“伦”之精义即在于个体之间的等差关系,因此,不妨说,在中国,个体乃是一个从具体、等差的关系角度出发去设想“旁人”的关系性存在。由于秉持着一种“关系取向”,个体就肯定不会是一个孤立的实体,而必是一个“社会的”存在。但是,个体的“社会特征”只有在等差的关系中方能获得有意义的说明。胡适指出,儒家想“人与人之间,有种种天然的或人为的交互关系。如父、如兄弟,是天然的关系;如夫妻、如朋友,是人造的关系。每种关系便是一‘伦’”。在各种不同的“伦”之下,每一个体都同其他具体的个体有着等差的、特殊的关系。无论“伦”是天然的还是人为的,每一个体都被期待着履行他的关系网络中的特定角色。我们在此应强调指出,在关系网中,个体同他人的关系既非独立的,也非依附性的,而是互依赖的。
因此,个体自我并没有完全失没于种种关系之中,相反的,个体有着广阔的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自主地行动。诚然,除了天然的“伦” ,如父子“伦”(在此种种关系中,个体的行为或多或少是由固定的身份和责任规定的)之外,个体享有相当大的自由去决定是否同他人发生人为的关系。而且,个体自我还能够塑造——如果不是决定的话——他同旁人之关系的种类。一言以蔽之,自我乃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实体,他能够为自己,为他人型塑角色,不仅如此,他还能够型塑群体的界线,而自我则是群体的中心。因此,诸如拉关系、攀交情之类的社会现象在中国社会如此普遍就不是偶然的了。这些社会现象都证明了个体在建构个人关系网时所享有的行动自由。行文至此,应再次强调指出,个体在建构个人关系网时把重点主要放在自己同其他具体的个体之间的特殊关系上,个体总是在一种特殊关系的基础上同他人进行交往的。在这种社会交往中,儒家“恕”的规范以所谓的“絮矩之道“(这是‘恕’的一种更为缜密的说法)成了主要的伦理向导。“恕”和“絜矩之道”的关键都在于“推”。的确,儒家伦理的核心就是“推己及人”,亦即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愿望推想他人的需要和愿望。按照儒家的思维模式,一个人可以由我推及家庭,由家庭推及国家,再国家推及天下。
但是,儒家的绝大多数价值规范都不是普适性的,就连无所不包的“仁”也很难解释成一种全面的伦理戒律。费孝通甚至认为,正因为缺乏一个定义明确的群体念,所以伦理无法发展出一个全面的、普通的道德体系。孝通的论断也许有些问题,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孝悌忠信四种基本美德全都是个人关系中的道德因素。在此赖世和()的观察也许是确当的:
中国人明确地承认普遍原则,但是另一方面却以强烈的特殊主义取向来冲淡它们。中国人的五种基本关系都是特殊的,不能普遍地适用。在各种美德中强调最多的是孝、和爱(或仁慈),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爱并非同等一律地适用于亲属和陌生人,而是按照特定关系的性质而审慎地分出等差来。中国人没有爱邻如爱己的观念。
儒家的个体只有在知道了他人同自己的关系之后,才知道应当如何同他人打交道。中国人在同陌生人打交道时常常感到窘迫不堪,这是一般人都认识到的。此一现象部分地可以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陌生人作为一个角色范畴乃是含糊不清的,因而就难以置于儒家伦理的任何一“伦”中。这就解释了中国人在建构关系的社会工程中为何把引介的方法作为一种文化机制来使用,通过介绍,个体便能够同陌生人建立起某种关系。我们可以说,儒家的社会理论未能为个人提供一个伦理向导,使其能够同与自己没有特殊关系的“陌生人”打交道。结果,虽然中国人似乎很讲究克制的功夫(即利夫顿所说的cult of ),但是在具体的家庭以外,他却有可能像世界上任何一个非中国人那样富于进攻性。艾伯哈特()写道:
由于中国人在家庭内部必须抑制其全部进攻性,因此外间世界就成了他发泄其进攻性的一个场所……只有同完完全全的陌生人在一起时,个人才是自由的,才能像西方社会中的个人那样自由地直接地发泄其进攻性。例如中国人在一个现代大都市或在外国同陌生人打交道时就是这样儒家学说思想核心在于而道家思想核心在于,因为他确知这种接触是偶然的,是不可能持久的。在这样的接触中,唯有进攻性的机智才是至关重要的,个人必须尽能经常不断地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同时又要避免冒太大风险。读一读中国移民特别是旅居其他社会的商人的传,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的确,在外部世界,当个体面对着那个称为群体或社会的混沌实体时,他发现自己不再是在结构上被置于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网络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儒家的价值规范在他看来似乎就不再具有道德约束力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一惯用语并不是一句会令人感到舰尬的话,只要把这句话放一个脱离了关系的社会框架中,它就不难理解了。中国人在同陌生人或群体打交道时往往都不再是真正儒学意义上的社会存在了。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社会现象,乃是个体常都并不把陌生人或群体视为一个严肃的关系对象,因此不能从相互依存的立场出发把自己同陌生人或群体联系起来。在这种情景下,个人也许就认识不到,当他从自身的道德或策略角度出发去看待问题时,这种视角往往要受到社会的限制,有时甚至在伦理上是不合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费孝通的“自我主义”的说法或许是有道理的。无怪乎当个人的生活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日益逮离家庭,自我主义便开始甚嚣尘上,泛滥成灾。而且,,毫不奇怪,在中国社会,个人主义这一术语不幸被界定为“个人第—主义”或“无纪律的自由主义”,意思是说,把“自己的荣誉、地位和利益高于一切” 。“个人主义”在台湾这个迅走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里已经成为一个十分严重的现象,上至于在一九八一年知识界开始呼吁除了传统的五伦之外,应当建立第六伦,亦即群己伦。这种试图为个体与群体社会之间的关系建立一项新的“伦”的想法本身再一次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亦即由于缺乏一个界定明确的“群”的概念,儒家的范典未能在社会与群体之间建立起可行的联系。因此,无论是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都没有在儒家的维模式中取得中心地位。但是,不管是好是坏,儒家的关系视角确实为中国人提供了—条途径,使他们能够创造一个期稳定的社会系统,而在此一系统中,个体乃是一个关系存在,被赋予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自主性,并置身于一复杂的、富于人情的关系网络中。作为中国社会中的一个人,他是很难逃离这个网络的。

本文选自金耀基著《中国社会与文化》(增订版)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选刊时,隐去原文注释,有需要参阅者,可参考原文。
随便看看
- 2024-05-11礼教与儒家传统的认知及想象主导着这场批判
- 2024-05-09明清思想转型暨纪念顾炎武诞辰41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江苏举行
- 2024-05-09儒家智慧梁涛 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七月廿八日壬寅耶稣
- 2024-05-08:中国文化何以有某些特点
- 2024-05-08北京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倪培民谈天地为己为人为天下
- 2024-05-082016下半年教师资格考试备考:明清之际进步思想
- 2024-05-08儒家人文思想暨第三届国际青年儒学论坛成功举办
- 2024-05-08高中历史必修三第一单元《中国古代传统主流思想的演变》
- 2024-05-07:先秦儒家和其他诸子百家对中国的影响
- 2024-05-07(每日一题)明清之际的儒家思想——宋明理学
- 2024-05-06儒家文化对当代社会的现实意义在于其道德价值,教育价值和政治价值三方面
- 2024-05-06中华三千年文明史上的很多东西,我们现在盖楼还用木制榫卯吗?
- 2024-05-05儒家的人生智慧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是对人生关注与思考
- 2024-05-04儒释道三教论西方学者评出“东方三大圣人”
- 2024-05-04(每日一题)孔子姓孔名丘
- 2024-05-04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形成,不能不提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 2024-05-03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术是如何被独尊起来的?
- 2024-05-03:儒家是孔子所创立、孟子所发展、荀子所集其大成
- 2024-05-03楼宇烈:儒家所讲的文化修养,首先是文化知识的提高
- 2024-05-03(李向东)孔子的“仁”与“道德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