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谈中国哲学思想问题追问不可能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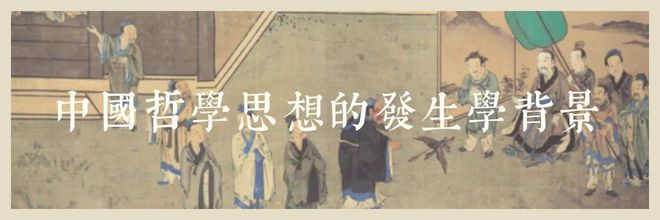

◎梁 枢
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
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
1
在发生学意义上讨论中国哲学思想问题,是一种对思想之原因的追问。显然,这种追问不可能局限于思想的范围内展开。因为,思想不能成为思想的原因,对思想之原因的追问只有超越思想,进人到思想产生的文化中去,进而深人到文化的基因层面才是可能的。诚如有学者所指出:
文化研究的深入,需要我们进入文化基因的层次。所谓“基因”,是借用生物遗传学的术语(英文是gene,这种研究不是着意赞美“元典”创造者的伟大心灵和崇高境界,而是研究这些元典产生的历史原因、条件和过程,从中发现隐藏在历史现象后面的必然性的东西。
如何深人到文化基因的层面呢?我们通常把思想称之为“流”,把思想所由形成的文化基因称之为“源”。如果把这文化源头严格限定在发生学的意义上,那么对它的追问是通过“沿流溯源”来进行的。
世界上有多个文明民族都有自己本原性的元典,如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圣经》,阿拉伯民族伊斯兰教文明的《古兰经》等等,也都需要“研究这些元典产生的历史原因、条件和过程,从中发现隐藏在历史现象后面的必然性的东西”。问题的关键在于“源”。“源”不同,“流”便不同。有什么样的文化,便有什么样的思想。所以,“沿流溯源”首先需要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源与流。
余敦康先生指出:
按照金岳霖先生的说法,中国哲学是“道”,希腊的哲学是“逻各斯”,印庋的哲学是“如如”。由于世界上的这三大哲学系列在开端之时就已经凝结了互不相同的最崇高的概念与最基本的原动力,所以在往后的发展中,也就形成了不同的运思方向,不同的思维模式和不同的总体特征。这种“流”的演变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不难理解。难以理解的是,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追本溯源,何以中国的哲学在众多的名词概念中竟然选择了一个“道”字作为哲学的突破口,而希腊竟然是“逻各斯”,印度竟然是“如如”?如果一部关于中国、希腊或印度的哲学史只是从开端处讲起,不去追求向上一路,从事探源性的研究,那么这种哲学思想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而真正的困难正是在“追求向上一路”,即发生学意义上的探讨。寻找本原从来就不是轻松的事。从文献的角度看,越靠近源头,材料就越缺乏,并且越需要对材料的可靠性作考察、辨析或解释。这一现象于古今中外都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就中国而言,对材料的可靠性的怀疑不仅表现于传世文献,近年来新近发现的出土文献如上博简、清华简亦无法幸免。常常是,一种“释疑”的可能刚刚发生,而“质疑”的声音也已随之响起。
与文献学意义上的“质疑”“相得益彰”的,还有一种惯常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于无形中进一步增加了“沿流溯源”的难度。在很多情况下,源与流总是被理解为各自有着固定属于自己的时间与空间,源只是源,流只是流,源在前,流在后,二者是绝对分开的。发生学意义的源头因此成了单一向度的存在;相应的,对源头的追溯也只能按照单一向度去进行。按照这样的逻辑,即使我们达到了文化基因层次,也仍然需要找出一定的文化基因所以形成的培育条件。与这个培育者相比,文化基因也还是属于“流”;而对于培育“培育者”的来说,培育者也仍然是个“流”。按照这样的定式去思考问题,“源”实际上被抽象化了,源与流之间有一个永远难以逾越的屏障。
对“向上一路”的追求,必须从这种抽象的思维方式中摆脱出来。
余先生的做法,是把五帝三王近两千年的历史看做一个连续的文化序列,并把它看做是中国哲学的发生学源头。
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各家哲学皆以道作为最崇高的概念与最基本的动力,普遍地追求行道、修道、得道。这个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其发生学的源头就是中国古代连续性的宗教文化。
这一结论以及它所蕴涵的方法,极具启发性,展现了中国当代学者在思想本原问题上的思考所达到的历史深度。
在我看来,其启发性在于,它把看似零散而杂乱的传世文献连贯起来,使之呈现出一个宏观的历史整体或总体。作为源头,这个历史整体或总体不是那个于时间、空间上先行独立存在的实体,而是与“流”,也就是与思想共行共存于历史文化之中的,是“源流一体”之源。于历史之外,没有什么先验的东西存在。相应的,我们对源头的追溯,不再是单向度的沿流溯源,不再是运思于历史之外,而是于历史之中,在流中求源。
我的上述理解强调了源与流的历史统一,而这样被理解的源流关系,实际上也就是思想与其形成的“背景”间的关系。为了论述上的方便,我想把自己在发生学意义上关于中国哲学思想问题的思考,从“源头”这个字眼,变成“背景”,即转为探讨中国哲学思想的发生学背景。这一转换的必要性在于,只有在“背景”的意义上,中国哲学思想的发生学“源头”,才能得到合理的说明。
2
《长安学丛书·政治卷》首篇选收了王晖先生写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篇旧作《季历选立之谜与贵族等级名号传嗣制》。这篇文章的价值在于,它于有限的传世文献梳理中,敏锐地发现了季立所以被选立的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因素,对于我们探讨思想史的“中国路径”,寻找中国哲学思想的发生学源头,提供了一个具有重要启发性的历史细节。
《史记·周本纪》记载,在歧周建国的古公亶父有三子:长子太伯、次子虞仲、少子季历。君位于兄弟相及,至于季历,最后传于季历之子姬昌。为什么会这样呢?《周本纪》曰:
太姜生少子季立,季立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端。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
小小的幼婴能有什么“圣端”?对此,清人崔述已怀疑过。王晖先生认为,文王之圣端,其真正原因在于他的出身,是“大邑”商族的外孙。文王之母是商畿内氏族显贵。文王头上因此便有了高贵的“天庭骨”,可以从母亲家庭里获得贵族的等级名号。古公预计幼孙昌会依靠外家的政治势力,迅速抬高周族在方国诸侯中的政治地位。所以做出了将君位传于昌父季历这一重大的政治安排。古公时代尚处于都邑国家文明的初级阶段,但到了季历时代,周人飞速发迹。季历对周边戎狄连连用兵,被命为“殷牧师”,征服了西戎;文王则被命为“西伯”。小邦周一跃而为西方大国,三分天下有其二,开始与殷人分庭抗礼。
亶父的想法和做法,以及最终的结果,证实了贵族等级的嗣承制在商周之际实际存在的历史事实。而这一历史事实则昭示了宗法血缘关系的资源意义。
中西方古代社会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有一个宗法社会组织结构。对此学界有着高度共识。上世纪四十年代侯外庐先生曾有精辟的概括。他说,古代西方的文明路径“是从家族到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古代中国的文明路径“是从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叫做‘社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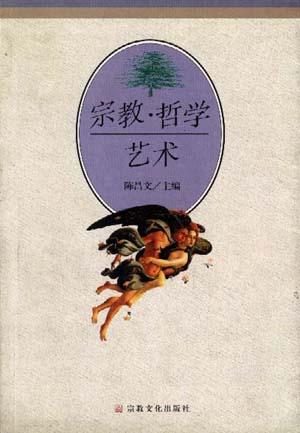
古希腊时代的城邦民主制是在摧毁了氏族制后建立的,氏族成员也因此脱离了氏族制脐带,而变为自由民小农。在这个过程中,以男性血缘为轴心的氏族组织形式,逐渐沦为要被摆脱、打碎和无可挽回地退出历史的旧制度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谈中国哲学思想问题追问不可能思想,血缘关系是步入文明时代的“障碍”。
与此不同,在古代中国,国家共同体的建设始终是在以父系血缘联结的家族——宗族结构基础上进行的。在这个过程中,血缘关系乃社会进步的“资源”,而且是可以不断被重复利用和深度开发的“可再生”资源。
于宗周时代形成的宗法制国家就是对这一资源不断进行历史地开发和利用的结果。这一结论,不难找到理据。谢维扬先生的《中国早期国家》在对“酋邦”这一核心概念进行论证过程中,实际上就为此提供了一种“历史的解释”;而余敦康先生在《夏商周三代宗教——中国哲学的发生学源头》一文中,则以“宗统”为核心概念,对此给出了一种“哲学的解释”。
余敦康指出,从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到含有初步分化和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到都邑国家形态,这三个演进阶段在中国文化中所表现出的最大的特色,就是宗族组织结构的出现。宗统是社会组织原则,其核心是父权的继承。它从总体上规定了宗法国家的性质。从颛顼到尧舜的五帝时代有社会组织无国家组织,有宗统而无君统。其基本特征是以王族的宗统来组建国家,垄断了公共权利的传承。公共权利的实质部分就是对全社会所普遍奉行的宗统的尊重、整理和维护。余敦康先生认为,五帝三王长达近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古代的宗教文化构成了一个不受权力转移和朝代更迭的政治事件的影响而自然生成的连续性的发展序列。这种宗教文化早期以宗族制度为依托,至三代时期则以宗法制度为依托。尽管经历了多次权力转移,但对宗统的尊重、维护、发扬却是一以贯之的,表现出文化的继承与延续。在三代所组建的国家中,宗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总体上规定了国家的性质。
这种对宗统的尊重、维护和发扬的过程,也就是把父系血缘关系当做资源不断加以历史性地开发和利用的过程,从而也就是古代中国的国家共同体建构的过程。
酋邦制实际上是这一过程的第一个阶段。谢维扬先生指出,从《晋语四》的纪录中可以看出,在黄、炎时期,氏族和部落实行的是父系世系制度。因为《晋语四》说到在黄帝的二十五子中概括儒家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这就是从父系本位出发来描述黄帝的氏族和部落的。而“酋邦”则是黄、炎时期实行父系世系制度的部落联合体的基本特征。即,所有部落事实上都依附和服从一个具有最高权力的部落的统治;这个最高权力部落的首领成为联合体即酋邦的最高首脑——帝或后。社会成员从平等的横向联系,演变成纵向的主从联系。
按照姜广辉先生所言,部落联盟,变做诸侯与天子的从属关系,这纵横的演变即阶级的出现。这应该是中西通例。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个横向变纵向的过程中,即部落间变为普通部落与最高权力部落的联系,最高权力部落的首领成为帝或后,父系血缘关系所呈现的不是“障碍”的意义,而正是资源的意义。两个横向变纵向,正是把宗统作为资源深度开发所造成的。这两个纵向是父系血缘关系本身所具有的运行取向。按余敦康先生的解释,父系血缘关系可按纵向列为九族。也就是以自己为中心,往上推四代,包括父亲、祖父、曾祖、高祖,再往下推四代,包括儿子、孙子、曾孙、玄孙。“这种九族制度用血缘亲属的网络结构把一些散漫的个体家庭凝聚成为组织严密的共同体。”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之上,有部落,部落之上有联盟,联盟之上有酋邦。整个社会形成一个以父系血缘为基础的共同体。
可见,横向变纵向的结果,并未像古代西方,氏族成员由此获得冲破氏族脐带,而成为自由小农的助力;恰恰相反,宗统没有被破坏,而是以这样的方式,得到尊重、维护和发扬。
至夏启,在酋邦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从宗统资源中开发出王权世袭制。父系血缘关系的资源意义进一步通过世袭制的方式呈现出来。借助这一资源,古代中国的国家共同体建设又向前迈了一大步。
在王权世袭制基础上,于父系血缘中再做细化,分出嫡庶,便有了宗法制。
至此形成完整的文化序列,也就指证了一个稳定的资源化背景的历史存在。在五帝三王长达近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宗统,即父系血缘关系始终具有资源的意义。这种资源意义表现为:
第一,父系血缘是宗法社会共同体的基本纽带。九族跨越阴阳两界,生死二轮,天上地下,把去世的亲人、在世的亲人,以及还未出生的亲人联成一个整体;把穷人(如崛起前周族)与富人(强族、王族)联在一起;把家与国联在一起。它协和万邦,把国与国联在一起;把不同宗族的人加以整合,使原本不是一家人的成为一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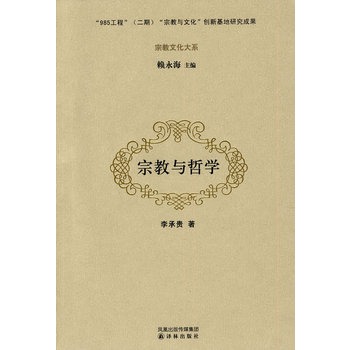
第二,父系血缘是宗法社会共同体的构建基础。宗法社会共同体的建设始终是在以父系的血缘联结的家族——宗族结构基础上进行的。宗法共同体在打破狭窄的氏族血缘限制的同时,又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建立了以父权的继承为核心的秩序结构,也就是从“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扩展为“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再而“有君臣然后有上下”,使宗统成为内外相通的社会组织原则。君臣关系以及宗法社会的各种关系不过是家族关系的延伸和扩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宗法共同体就是一个以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大家族。
第三,宗统或父系血缘构成宗法社会共同体的轴心,是向心之心。共同体的所有“公事”无不同时是“家事”。如宗教事务、外交、经济、政治等。
第四,宗法社会共同体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一种“宗法性存在”,对于这个大家庭的普通成员来说,“宗法性存在”是一个只能接受而无法选择,更无法撼动的既成事实,是他们从事文化创造的既定的历史前提;而对于同样是作为“宗法性存在”的共同体家长而言,以公共权利尊重、维护、发扬宗统,建设一个更为完备、更加强大的宗法共同体,则是唯一和必然的选择。
第五,宗法共同体的建设同时也表现为一种“思想过程”。思竭的形式是宗法性宗教。其最初的表现是,伴随着各个分散的宗族组织向一个统一的共同体过渡的历史过程,一种为大家普遍认同的共同宗教信仰、共同理想逐步建立,最终成为共同体的观念形态。
3
宗统或父系血缘不仅为社会共同体提供“资源”,同时也提供“问题”。
在歧周建国的古公亶父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迅速抬高周族在方国诸侯中的政治地位,使自己的家族从弱小的群体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展为显族、强族;而解决之策也只能从周族的宗法性关系中去寻找。换言之,宗法性关系既是他的资源之所,也是他的问题之所;既是解铃者,亦是系铃人。资源化背景和问题化背景不过是他所处环境的两个方面,或两个属性。
以此观点再读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也会读出同样的东西。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嫡之子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通婚之制。纵观这三个制度建设,哪个不是由宗法关系性存在而发生,哪个不是为解决宗法性关系问题而建立,哪个不是从问题所产生处寻求问题的破解之策?
宗法性社会问题重心在于人、社会。宗法不是别的,就是在共同体建设过程中形成的用来调整宗族内外关系的制度原则。它脱胎于以男性血缘为轴心的氏族组织形式,是处理宗族事务的原则,伴随着共同体的建设,它从宗族内扩展到了宗族外,等于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是一个复杂的人际关系结构,从中每时每刻都会产生大量的以人际关系为主题的“家务事”。古代社会,无论中西,“乱”与“治”的相互转化都是一个恒久的主题,但其历史内涵却大相径庭,文化属性判若云泥。在古代中国,“乱”是“兄弟阋于墙”(《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而不是异族仇恨;“治”是亲亲、尊尊而不是什么阶级专政。
从夏商周三代前后相继的发展实质,是建构更加完备从而也更为复杂的共同体,“家务事”因此明显地呈现由简到繁的趋势。
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同,使得问题的提出方式各有不同。但是如何形成和谐的社会关系,如何建立良好而有效的社会秩序,如何维持长治久安的社会状态,一句话,如何尽人事,却是宗法性社会所面临的一以贯之的基本问题。五帝时代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官天下”,即如何跨越血缘组织的先天局限,把分散的宗族统一成为有着共同意志、共同理想的文化共同体;而三王时代则是如何“家天下”,即如何解决一姓与万姓关系。但究其实质,如何利用宗统或父系血缘关系这一资源概括儒家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来构筑宗法社会共同体——这一难题成为五帝三王长达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共同的“问题化背景”。
4
资源化背景与问题化背景稳定的历史联结,使得宗法性社会共同体成为长时段的历史存在。从宏观与总体上,对中国文化与思想基本走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于发生学的意义上,决定了文化与思想的基本方式与基本面貌。
在中西两种文化与思想方式之间存在的若干差异中,宗法组织结构因此成为“本体性”差异,与中国特有的文化方式、思想方式之间产生重大的关联。考古研究表明,人类在其童年阶段,文化与思想还处在初步发育阶段的时候,的确经历过一个以相似性为基本特征的时期。在进入文明时代之时,中西文化在共同发展中逐渐出现了“分岔点”,并由此形成了各自的思想轨迹,为历史留下了两张迥然有别的“思想路线图”。而对于中西两种文化方式与思维方式而言,宗法性组织结构这个差异点是“本体性”的,其他的种种特质都围绕这一“本体性”差异而发生,都要通过它的存在而各安其位,并得到最合理的说明。
由于宗法共同体成为长时段的历史存在,古代中国人的思想也就只能长时段地作为“宗法性存在”而存在。反言之,如果没有宗法性社会关系从资源与问题两个方面,为宗法社会共同体提供稳定的“本体性”支撑,中国思想史以及它的书写方式,都会因此完全成为另外的样子。
在两个背景交互作用构成的历史平台之上,以公共权利尊重、维护、发扬宗统,持续不断地进行宗法性共同体的“制度化建设”,成为横贯五帝三代长时段历史的主轴、主线。在这一主轴、主线作用之下,思想只有作为宗法共同体的观念形态孟子研究院特聘专家谈中国哲学思想问题追问不可能思想,才有合法性,才能发挥作用。
第一,思想的主体是宗法性存在,其身份体现宗法的限制。其中思想的最初主体“祝”、“宗”等神职人员没有形成独立于社会生活的教团组织,这一点与西方和世界上其他宗教有明显的不同;
第二,思想的内容也是宗法性存在。制度的思想形态是观念、原则,这些观念是人们从发现问题至解决问题的认识过程中,对历史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升华得到的,制度不过是思想的外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生和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数是学,末度也是学,所谓王官之学,只有内在地把末度之学作为其前提和基础,才能成立。
在古代,这些观念、原则隐藏于宗教形式之中,人的本质力量外化过程因此表现为向天神投射的过程,因而我们需要从这种投射的轨迹中寻找思想发展的脉络。这是中西思想发展的通例。与西方思想发展形态不同的是,中国古代宗法共同体的观念、原则未能以独立或完备的观念形态而存在,而只能附着于制度形态或物化形态。因此我们了解古代中国思想的脉络,不但需要从其宗教形式中抽取,还要从制度或物化形态中加以剥离。
在共同体的建设中,“宗法性存在”是一种对文化方式和思想方式的塑造,其中内含对人对思想主体的塑造。是一种培育之功。它表现为一种秩序、制度和关系结构的建设;也表现为一种思想建设。它附着于实践及作为实践结果的秩序、制度、礼仪或祭祀活动和关系结构之上,并以宗法性的宗教的形式存在,是属神的而非属人的。而在我们对之进行思想史分析时,才呈现为一系列原则、观念。
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原则、观念被不断被赋予理性的形式,而得到完善与升华。
第三,共同体完备形态是道术统一,内外贯通的,相应的,这些观念、原则“其运无乎不在”。它们犹如五官,各司其职,在共同体中结成一体。也只有在相互联结和互动中,才有自己。共同体是思想的家。《诗》以道志,是道共同体之志,《书》以道事,为共同体之事。共同体分裂,则道术为天下裂。
第四,这些观念、原则在五帝至三王的长时段历史中“一再被肯定”,而成为传统。
对于第四点,进行一下展开性论述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内含着本文的主题——中国哲学思想的发生学背景的价值内涵。
对于传统的形成,有学者指出:
当我们考察历史上的文化积累和变革时,我们会发现一些相对稳定、长期延续的内在要素,它们在文化积累中一再被肯定,在文化变革中也仍然被保留,我们把这样的东西称为文化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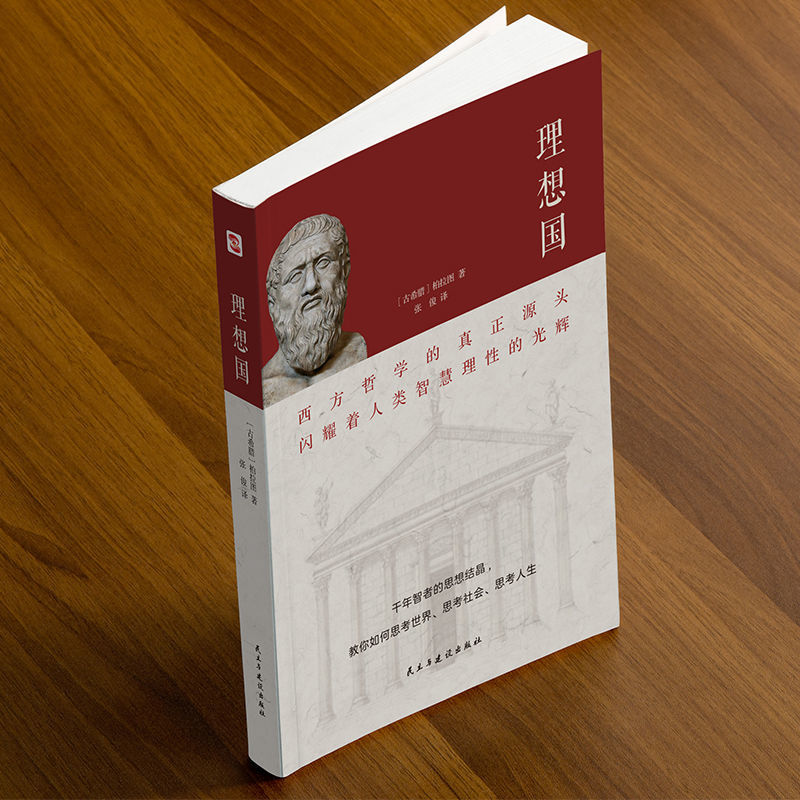
简言之,何为传统?被一再肯定的思想就是传统。那么什么样的思想被一再肯定呢?比如,
所谓“五典”……,指的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人文价值第一次从九族制度的组织原则中开发出来,……超越了不同族别的血缘谱系的狭窄的界限,而具有普遍的伦理意义。……这种宗教伦理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儒家思想的发生学的源头。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五典的思想被开发出来以后,至迟于轴心时期被儒学以“源头”的名义再一次肯定。
再比如:
要解释儒学构成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原因,我们以为应从古代社会结构着眼。从根本上说儒学适应了中国古代血缘家族的社会结构。……是血缘家族社会观念的升华。
这就是说,儒学成为主流文化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源于古代血缘社会的观念,以升华的方式被一再肯定过。
也有一些传统,比如“家为巫史”,曾经在一段历史时期中被一再肯定,大行其道。但“绝地天通”将之废弃,逐出历史舞台。这之后便不再是传统。
把这一例子与前文所引“春秋战国时期,儒墨道法各家哲学皆以道作为最崇高的概念与最基本的动力,普遍地追求行道、修道、得道。这个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衔接起来,便对所谓“道”有了一种很直观的认识:道者,一以贯之者也;所以一以贯之,一再肯定使然也。先前曾经是道,后来没有人走了,就是废道了。废道,非道也。废道,就不构成我们这里所说的“传统”。
这些“一再被肯定”的传统跨越时空,于漫漫的历史进程中一脉相承,一以贯之。这一情景一再出现,使得我们在了解和学习这些传统的同时,自然而然就会引起我们的另一种关注:在传统的背后,那个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一再肯定”同一个传统的“肯定者”到底是什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个“肯定者”一再肯定同一个传统?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被称之为“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建构”的讨论中去。这场讨论的价值取向与学术取向在于,以西学作为稳定的参照系,利用传世文献与新的考古发现,展开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揭示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的本原,从根本上回答中国人是谁的问题,从根本上解构西学东渐百年以来的文化认同危机,为在中西比较背景下书写的中国思想史、文明史提供主词。一言以蔽之,这场讨论就是在寻找“一再肯定者”。
“一再肯定者”是中国人的精神内核,价值世界的最后归宿,多重精神的联结者,中国文化的内在逻辑所在。
“一再肯定者”是古代思想家所有思想命题及概念的根据与本体。它隐身于这些命题背后,是形上者。由于表述者各异,这个“一再肯定者”被以不同方式表述。《天下》篇称为“古之道术”、“古人之大体”,与命题的关系表述为“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王国维先生《殷周制度论》称之为“道德团体”;安乐哲先生称之为“策源地”。
类似的表述还有很多。如果从大的历史尺度看问题就会发现,当代的表述者与古代的表述者,甚至包括尧舜时代五典的最初表述者实际上都在重复着同一件事情:他们于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表述,都只是“一再地肯定”同一个事实:古代的思想是宗法共同体的观念形态。换言之,古代中国人思想观念不过是宗法共同体的观念形态这一必然性的事实,会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的学者那里,获得不同的表述。在这些不同的表述及表述者背后的才是那个真正的“一再肯定者”。这个“一再肯定者”不是别人,就是横贯五帝三代历史的宗法共同体。它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文化方式与思想方式的“一再肯定者”概括儒家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是因为,它作为宗法社会的问题化背景和资源化背景的提供者,被历史一再地选中。因而,一再地从资源与问题两个方面,为历史提供稳定的“本体性”支撑。
文章选自《国际儒学研究》

随便看看
- 2024-05-16李尼佛福:色即是空,空即色
- 2024-05-13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础是阴阳五行学说是什么?
- 2024-05-12风水堂:舍得,得舍。何得?
- 2024-05-12不二和尚:老子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人本化进程,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 2024-05-11先秦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史:精耕细作农业的形成模式
- 2024-05-10:适性人生哲学行了具体阐释——z
- 2024-05-10中国绘画渊远流长,博大而精深,花鸟画的文化体系
- 2024-05-09香港大学弗洛伊德的50本经典书籍目录及简介
- 2024-05-08:中国文化何以有某些特点
- 2024-05-07:先秦儒家和其他诸子百家对中国的影响
- 2024-05-06中华三千年文明史上的很多东西,我们现在盖楼还用木制榫卯吗?
- 2024-05-05广州大佛寺经常举办癌症康复营,颇为好奇!
- 2024-05-05南怀瑾老师:佛教的生死观就是苦的体现,不再受生死轮回之苦
- 2024-05-04以教材为范浅谈高中学段议论文写作教学策略
- 2024-05-02(知识点)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的代表人物和思想
- 2024-05-01(荐读)10个佛家智慧要点,一起来精进!
- 2024-04-3010个智慧心语,一起来品读,开悟,修行
- 2024-04-30探寻生死之间的哲学:周国平与佛教的不解之缘
- 2024-04-29佛家的智慧就是哲学 春色无高下,花枝自短长,蔷薇和玫瑰怎么能比较?
- 2024-04-29南怀瑾老师:佛教是宗教,亦是哲学?什么是真?
